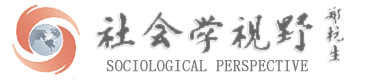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联系电话:010-62511143
京公网安备110402430004号 京ICP备05066828号-1 邮箱:sociologyyol@163.com 网版权所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
|
|
乡村社会的魅力
信息来源:
作者 卢周来
我上篇专栏文章说到了农民工春节往返于城乡之间的悲壮迁徙。有一位朋友读过此文后电话里对我说,他12岁随父亲进城,老家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亲戚朋友了,但不知为什么,四十多年过去了,他认为他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还是当年那个贫穷的小乡村,至今魂牵梦绕的也还是那个地方。每年清明他还会回去给爷爷上坟。尽管下飞机就有小车接,回乡的路一点不悲壮,但那种回乡的迫切感与农民工无异。不过,这位朋友接着又说,尽管如此,让他现在重新回乡村生活,他已经不习惯,也不愿意。
相信许多城里人都有我这位朋友类似的心境:有思乡病,却无居乡心。也正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嘲笑这类人是“叶公好龙”,甚至有人说得更刻薄:认为是一些知识分子想把乡村作为“活化石”,好满足这一群体“畸形”的审美感。实质上并非如此,从思想史角度看,有许多学者早已指出,乡村社会对于城里人来说的确具有精神上的需要,而这种精神上的需要说到底又来自于现代经济生活造成的内在紧张。
在中国学者中,我见到过对于乡村与城市关系较早的但最为深刻的论述应该是
作为文化大师,
但
从“向往自由”角度解释乡村社会魅力的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公共选择理论代表性人物之一的布坎南,在其名著《财产作为自由的保证》一书中,他论述道,乡村代表着农业社会。而因为农业社会中人们靠自给自足生活,因而几乎具备完全的独立性,也是人类历史上生活最自由的阶段。这种生产是“伊甸园式”的。但在农业社会后期,人们逐渐通过此前少数专业化与交换的经验发现,专业化能提高生产效率,并更好地改进了福利。因此,专业化与交换经济进一步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人类历史上一种生产方式的大变革: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经济转向基于分工与交换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也是基于契约实现的经济。
最后,专业化与分工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家庭,能够在市场之外的、与世隔绝的自给自足状态下生存。”这对参与者最大的不同是,在自给自足的条件下,人们“仅仅依赖于它自己的选择以及自然秩序的力量”,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加交换必然造成对他人行为的依赖。即便不存在强制,个人的福利必然受制于他人行为造成的变化。”
而正是这种“依赖的不对称性”,使得“一些参加者甚至是在完全自愿的交换当中,也可能受到他人的剥削。正是这种依赖关系似乎为剥削创造了潜在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要摆脱自愿但不公正的契约,唯一的通道在于参与者能否有“退出的自由(Freedom of exit)”。即“当个人认识到参与缔约受到了伤害,并通过保留退出市场依赖关系机会而放弃一些由专业化所带来的利益”。
此时,如果人们保留了土地,那么,如果他认为契约导致的分配不公正,他完全可以退出他的市场交换而回到自足状态。而恰恰土地又是乡村社会最大的资源。正因此,不自由的状态使人们怀恋乡村社会的自由,而要摆脱不自由状态还是依赖于乡村社会中能有“自留地”。正因此,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对乡村的依恋是有足够理由的:其背后是对农业社会“伊甸园式”生活中自由的向往!
也因此,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布坎南甚至也从他的角度理解了马克思:“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之所以提出这种理论,理解为对个人因进入市场交换关系而远离自给自足的个人、家庭或小社会的田园诗般的独立生产而导致失去自由过于敏感。由于这种敏感性,马克思成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一部分。”
看来,乡村社会最大的魅力,正是因其代表着人的彻底自由。在这一点上,大师们的心与中国农民工的心都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