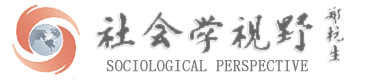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联系电话:010-62511143
京公网安备110402430004号 京ICP备05066828号-1 邮箱:sociologyyol@163.com 网版权所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
|
|
城市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王国伟
文章来源于:《文汇报》2013年3月。
城市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在陶醉于增长的热潮中,我们走到了城市发展和更新相互交织的十字路口,物质和精神,历史与现实,在城市建设推进中,始终充满着冲突和矛盾。发展中的城市,需要更新和重构。
那疯狂糟糕的时刻,
那滋生罪孽的城市大缸,
是多么的不可或缺。
试想,某日从雾和灯影深处
一个新的基督光耀照人地降生,
他高举起人性,
用新星的光焰将它洗炼。
——维尔哈恩
比利时作家维尔哈恩《触角般的城市》中表达的对城市无可奈何的感叹,以及隐喻中强烈的悖论,诱惑并推动我们去关注并穿越城市发展的历史。而当我们直面朝夕相处,又若即若离的现实中的城市时,没有一本书如《收缩的城市》给我带来如此的震撼。这本集合了多学科智慧、多维度思考、从城市宏观思维到有说服力的个案分析,给出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城市一味增长的时代结束了!同时,又把我们打回到思考的原点:城市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从中国发现最早的距今约6500年前的大溪文化时期的城市遗址(现湖南澧县遗址),到世界近现代城市几个百年轮回,城市化依然是地球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选择。全球约近30亿人口装在这个容器里。而中国过去的30年,把5亿农民送进了城。城市化依然被视作人类去往理想彼岸的现实版诺亚方舟。
与人类文明相伴相随的城市,与众生祸福相依的城市,到底是什么?是容器,是空间,是舞台,是市场?不同的学科会给出不同的定义和解释。唯一能在表达上不产生歧义的共识是,城市是人造体,是人类创造的一个生命容器,是人类建构并满足各种交流的公共空间。人是社会性动物,人需要交流。从最初的物物相易到现在的信息交换,从经济文化的传递,到人类感情交往,城市成为最好的载体。
同时,城市还造就了兼具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城市空间。不同阶层、不同角色,形成了交流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公共性依赖标准和规则,不但形成交流的可能和有效,也提供人发展的可能性和社会参照样本,以及自我和社会价值的评价标准。而城市给人带来更大诱惑的是,在公共性及其规则背面,有一个更大的私人和精神空间。大隐隐于市,其实就是人类对这种独立空间的寻找。但城市在缩短人的物理距离同时,却拉长了心理和情感距离,让生活和人生多变、丰富起来。不可捉摸,这正是城市空间的可塑性和魅力所在。
不同的交流需求,需要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城市构成的多元复合空间,使人的需求有了丰富性和层次感,私密与公共的关系,不但是物理的,而且也是心理的,而且会随着人的心理、情绪随时转换的。就像人们去咖啡馆,除了喝杯咖啡之外,这里可以释放内心的焦虑,也有更多的社会信息可以在这里被输出和植入,咖啡馆内人与人之间形成的若有若无的关系,这种公共性与私人性兼顾的场所,构成了城市人互为依存的特殊联系方式,产生了城市人的客厅效应。更有甚者如海明威、萨特等作家和学者,他们喜欢泡在咖啡馆里写作,甚至都有专坐,就像一个生命密码被复制在了这个空间里,他只需要循着生命往返的气息,就可以准确地到达属于他的位置。而狄更斯更是城市忠实的信徒,在外时间久了,就想念城市,与城市的周期性接触才能使他保持内心踏实和创作灵感的鲜活。这种感觉大概就是诗人波德莱尔对城市既清晰又模糊的界定:不知是城市集聚了“人群”,还是“人群”造就了城市?
“人群”是城市最基础也是最典型的符号和元素,城市的开放性和私密性是“人群”聚合的两个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是人性化的,是暗合了人的这种本质需求的,况且,城市人面对乡村有着明显的政治和层级优势,因此,城市是“由人构成的机制创造出的一片乐土”(本雅明语)。
但城市毕竟是人造体,有生长、成熟、平缓、衰退的生命周期。城市在不断满足人们的需求时,也生产着无尽的欲望。“产业结构调整、移民梦想破灭、环境资源的失衡、管理政策的失误,都可导致城市衰落”。城市在发展和提供一切便利时,也在产生着交通、治安、环境等众多问题,这些与工业革命同步的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依然还在被不断的重复。而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城市对人口有限的容纳能力,交通、住房、医疗、教育等,产生着巨大的不适应性,因此,这种矛盾和冲突制约着制度的进一步开放,又反制着外来人口的短期性和周期性。
这种城市生存危机,尽管直接反映在物质和物理空间层面,但实际带来的是城市人心理焦虑和安全感丢失的整体性恐慌。当城市的肌理被不断腐蚀和剥落,人在城市的生存空间也就不断被挤压。当年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还会演绎出各种现代版本:无数的人要冲进来,不少人却在设想如何逃离这个飞地。
“熟悉的城市如同幽灵般向‘闲逛者’招手。在这个幽灵的召唤中,城市时而变成一道景观,时而变成了房屋”(本雅明语)。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城市人基本是移民构成的。城市对每个落脚的新人而言,是梦幻如景观,又现实如房屋,这种空间的恍惚和时间的漂移,就构成了城市人的虚幻感,艺术就成了城市这种虚幻感的最好诠释者。从波德莱尔的巴黎旧梦,到弗里茨·朗的经典默片《大都会》,再到伍迪艾伦的早期都市三部曲《安妮霍尔》《曼哈顿》《汉娜姐妹》,半是虚构、半是事实的艺术表现,能使各个阶层,面对同一个问题,构成同一种理解城市的纬度。
城市的丰富性和文化厚度,城市生活的多元和生活方式的多层次落差,往往成为艺术取材的不尽源泉。波德莱尔把大众看成是隐形的城市存在,他描写的带有某种神秘感的巴黎女人的病态美,入木三分的勾勒出城市的特殊气质。而作家爱伦坡在他的小说里,“人群中的人”是他对城市基本意向的归纳,面无表情、过度反应,在他的笔下已然是匆忙的城市人的基本状态,也进一步把人和商人组合到一个既同一又分裂的���格模式之中。而到了普鲁斯特,他从波德莱尔诗里读出了神秘的巴黎女人,“是巴黎街头上神秘一瞥就能看到和感受到的,身体裹在黑衣服里,面无血色,略显苍白,手指纤细而有形的形象”(本雅明语)。我们从这种意向中,不难想象这是晚上纸醉金迷,白天昏昏欲坠的生活图景,更能从中读出城市人的孤独和冷漠。这种颠倒和迷离,也正是大城市的魅力所在。难怪伍迪艾伦乐此不彼,总是喜欢把镜头对着城市。到了21世纪,我们看到他的新城市三部曲《爱在罗马》《午夜巴塞罗那》《午夜巴黎》时,他不但以艺术的方式跟踪着城市的变迁,也对城市的艺术解读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他把讽喻和城市景观结合,他把历史与现实交错,他炉火纯青的艺术表现力,已经把城市解读提升到一种至高的艺术境界。但是,尽管伍迪艾伦用艺术的方式,不断对城市与历史形成穿越,但我们眼前的城市,却更加迷离、更加难于捉摸。
“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美国电影,就其对城市的表达来看,被归纳并定格为‘灰**’流派”,灰色是城市电影的基本色,灰色是艺术家和城市人对城市的基本判断。在经典灰**中,“城市是紧张的、垂头丧气的、个人孤立集体混乱的地方”。如果说,城市蓝调和节奏布鲁斯是产生于美国中西部能看到的、也是最醒目的,一望无际的田野和大烟囱城市背景,那么,摇滚、朋克则是来自于身体与狭窄的城市空间碰撞而产生的另类解读。音乐的节奏与城市的节奏表现出天然的相关性和一致性。
艺术视角中的城市,正面是天堂、背面是地狱,就如依靠主题灯光给夜晚的城市以装饰性,让人们陶醉于纸醉金迷的繁华正面同时,难以遮蔽贫困、破败、肮脏和丑陋的背面。艺术只能让人经历遗忘,却无法给出答案。
看来,对城市的思考,需要逆向思维。《收缩的城市》就提供了这种思考的参照和样本。在陶醉于增长的热潮中,我们走到了城市发展和更新相互交织的十字路口,物质和精神,历史与现实,在城市建设推进中,始终充满着冲突和矛盾。发展中的城市,需要更新和重构。更新依然是从艺术干预方式开始。艺术成为挽救城市工业废墟,化腐朽为神奇的第一根稻草。业已基本瘫痪和废弃的工业园区,使用成本低廉、自由,管理方式宽松,使得大量流浪艺术家、草根艺人、非主流先锋派、个体自由职业者,成为进入的先行力量。他们进入方式是民间的、自然的、个体的,反而构成了特殊的民间艺术生态效应,其形式的丰富性与草根特点,又为拉平地区、贫富的级差,提供了可能性。
但城市建设中,势必会形成“不可估量的身份和意义的逐渐丧失。”虽然空间在不断被重构,却造成了“集体记忆”的缺失,进而引起“思想的收缩”。随着本土文化从城市界面上逐渐消失,人们必然会在撤回私人空间和退避文化的两个基点上,产生出三个选择的维度:离开、留守,还是返回?看来,面对城市,我们依然爱恨交加。
(作者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