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学
年轻人对移民更友好吗?对香港和上海的“世代—双城”比较
摘要: 对移民态度的问题,已有研究提出了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心理学两大流派的多种具体理论假设,但忽略了“世代”这个重要的分析视角。一些研究发现年轻人对移民更友好,另一些研究发现并非如此,这表明,对世代效应的识别和解释必须联系年轻人所处的具体经济社会情境。本文首次对香港和上海进行“世代—双城”比较,并整合验证了已有文献提出的宏观经济环境、个体经济利益、财政或福利负担、群体威胁或接触、地方和国家认同等重要解释。研究发现,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确实使香港和上海的年轻世代对移民的态度呈现鲜明反差:上海的年轻人对移民更友好,香港的年轻人对移民更排斥。
关键词:移民 世代 香港 上海
移民对流入地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等积极的一面,也有造成资源和群体关系紧张等消极的一面。本地人对移民的态度是我们了解移民对流入地社会影响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对于本地人对大量涌入的移民群体的态度问题,在移民历史悠久的欧美学术界已有许多研究,并对态度形成机制做了理论归纳和解释,但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还比较少,大多数研究只是从农民工或外来人口的角度探讨移民群体如何融入城市(郭星华、储卉娟,2004;张文宏、雷开春,2008;杨菊华,2009;崔岩,2012;李培林、田丰,2012),少有研究从本地人口的角度考察他们对移民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其中,从世代角度的分析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本研究以香港和上海两个城市为例,结合21世纪以来两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境,从“世代—双城”比较的角度探讨年轻世代对移民的态度是更加友好还是更加排斥。
一、对移民态度研究的两大理论流派
国外对移民态度这一议题的研究相当丰富,目前已有两篇综述就这一议题做过详细的回顾与展望(Ceobanu and Escandell, 2010;Hainmueller and Hopkins, 2014)。其中,根据海因米勒和霍普金斯的观点,关于移民态度的研究主要沿着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心理学两条主线展开,并形成了一系列经典理论或假设。
(一)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经济因素对人们态度的影响,包括劳动力市场竞争假设、财政或福利负担假设、宏观经济状况影响等。
劳动力市场竞争假设的主要观点是,掌握同等劳动技能的本地人与移民是相互替代的,所以人们对移民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相对位置。具体表现为:本地人倾向于反对与自己持有相似劳动技能水平的移民,而不反对与自己技能水平不同的移民,低技能的本地人更倾向于限制移民的政策(Scheve and Slaughter, 2001)。有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该假设,即低技能的人更加反对移民(Mayda,2006)。但更多的研究发现,无论本地人自身技能如何,他们对移民类型的偏好都是一致的,即普遍欢迎高技能移民而反对低技能移民,同时自身技能较高的本地人对所有技能水平移民的态度都更加宽容(Hainmuller and Hiscox, 2007,2010;Hainmuller, et al., 2015)。海因米勒和霍普金斯(Hainmueller and Hopkins, 2015)明确指出,美国人有潜在的移民偏好共识,即更欢迎受过良好教育以及拥有较好工作和社会地位的移民。赫尔布林和克里希(Helbling and Kriesi, 2014)的研究也发现劳动力市场竞争假设缺乏支持,并研究了人们普遍喜欢高技能移民的原因。
财政或福利负担假设可以视为劳动力市场竞争假设在财政或社会福利领域的延伸。其主要观点是,低技能移民会对公共财政造成负担,也会增加本地人的税收负担,高技能移民则相反。对美国的研究发现,在财政负担更高的州,更高收入的本地人对移民表现出更低的支持(Hanson, et al., 2007)。跨国研究也印证了这一观点,更高收入的本地人关注移民带来的财政负担,并对移民表现为较低的支持(Facchini and Mayda, 2009)。另有研究发现,没有工作计划的移民被认为是更加消极的(Hainmueller and Hopkins, 2015),背后原因可能也与财政负担有关。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关注宏观经济状况对人们移民态度的影响。欧洲的跨国研究发现,对国家社会经济安全乐观的人持有更加积极的移民态度(Paas and Halapuu, 2012)。在呈现增长态势部门工作的受访者更加支持移民,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移民大量涌入的部门反对移民的人数略有增加(Dancygier and Donnelly, 2013)。加拿大的研究也表明,在国家经济稳定繁荣时期,人们对移民的态度普遍较为积极(Wilkes, et al., 2008)。但在宏观经济下滑时期,人们对移民的态度则趋向消极(Ruist,2016),即使是具有高教育水平的人也是如此(Goldstein and Peters, 2014)。因此,国民经济景气状况(包括人们对国民经济的感受)成为移民态度的一个预测指标(Citrin, et al., 1997)。
(二) 政治心理学
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先是从群体心理角度进行解释,主要有“群体威胁论”和“群体接触论”,它们都是关于偏见的理论(Fussell,2014)。威胁和接触可以看作群体理论的两个方面,共同点是从社会心理角度将本地人和移民理解为两个界限相对分明的群体,但在群体间互动以及结果的解释上存在差异。
“群体威胁论”认为,当外来移民达到一定规模时,移民和本地人两个群体之间会围绕稀有资源展开竞争(Blumer,1958)。移民对本地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可能产生威胁,包括实际威胁和感知威胁。当本地人感受到这种威胁时,就会对移民产生消极态度(Haubert and Fussell, 2006;Escandell and Ceobanu, 2009)。“群体接触论”则认为,移民群体规模越大,群体间接触的机会也就越大,而群体接触可以缓解两个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削减本地人对移民的消极刻板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本地人对移民的态度转向积极(Pettigrew,1998)。进一步的研究认为,群体接触及其效果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类型与质量的接触对改变消极态度的作用并不一致。例如,本地人与移民成为朋友或存在亲密关系可以明显增加他们对移民的好感(McLaren,2003;Hayes and Dowds, 2006),但本地人与移民在工作场所的接触对态度改观没有显著效果(Escandell and Ceobanu, 2009)。不少研究都表明,群体威胁和群体接触的效应是同时存在的(Schlueter and Scheepers, 2010;D’Ancona,2018)。更有学者将威胁与接触两个理论同时整合进时间与空间的框架,发现群体威胁效应和接触效应在不同地理层次上占据的主导地位不同,在国家和邻里层次上主要是移民涌入带来的威胁效应,但在中观的地区层次上主要是移民接触带来的积极效应(Weber,2019)。
政治心理学流派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是社会或国家认同理论(Tajfel and Turner, 2004),它是指人们对于自身所属的社会有认同与偏好,进而对其他社会/民族/国家的人有偏见或歧视。生活在多民族国家的人还存在双重认同问题,即国家认同与次国家单位认同(或地方认同)的兼容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地方认同与对移民态度的关系就取决于认同背后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例如,对比利时的研究(Maddens, et al., 2000;Billiet, et al., 2003)。比利时的瓦隆和佛兰德是两个具有高度自治权的经济大区,两地居民都具有高度的地方认同。但是,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兼容性在这两个地区有明显差别。瓦隆大区政府在对外国人的态度导向上与比利时国家政策整体保持一致,即支持多种族的和平共存,因此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不存在明显冲突,或者说存在地方和国家的双重认同。而佛兰德大区深受极右主义的影响,地方认同具有种族中心主义倾向,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巨大张力,因此,当地人的地方认同越强,国家认同就越弱,对外国人的态度也就越排斥。类似地,英国的苏格兰也是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紧张或冲突的典型地区,强烈的地方认同或地方主义倾向导致当地居民对外来移民怀有强烈敌意(McCollum, et al., 2014)。
二、世代:被忽略的分析视角
上述理论假设和经验研究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分析视角——世代。对移民态度的量化实证研究大多只是将年龄或出生组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很少作专门讨论。这些研究大多发现年轻人对移民更友好(Schotte and Winkler, 2018),但对这一结果,既有年龄效应的解释,也有世代效应的解释(Hello, et al., 2006;Ford,2011;Ross and Rouse, 2015)。前者是指,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们的观念和态度会变得保守,因此,年轻人对移民更包容,老年人对移民更排斥。后者认为,年轻人更包容移民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年轻世代普遍教育程度更高,接受了自由主义观念;二是他们在多种族环境下成长,对外来族群更熟悉;三是由于前面两个因素,他们自幼就与移民及其后代有所接触,感知的威胁更小。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在方法上并没有区分到底是年龄效应还是世代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少量研究并不支持年轻人对移民更加友好的结论,这给世代效应的本质或方向问题打上了问号。对25个欧洲国家的研究发现,虽然大多数国家的老年人更加反对移民,但希腊、爱尔兰、以色列和斯洛伐克等国家的年轻人更加反对移民(Schotte and Winkler, 2018)。对美国、英国和希腊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年轻人的反移民态度与某些特定因素相关。通过对2006—2009年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生对无证墨西哥移民态度变化的考察发现,随着金融危机期间失业率的逐年上升和GDP的增速下降,大学生反对无证移民的情绪也在增加(Diaz, et al., 2011)。围绕苏格兰人对移民的态度和苏格兰政府移民政策的研究发现,最年轻的一代苏格兰人(18—24岁)表达了最强烈的反移民态度,苏格兰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比老年人强烈(McCollum, et al., 2014)。2003年,有学者对12—17岁的希腊青少年调查后发现,他们存在比较严重的反移民倾向,并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希腊的学校缺乏系统的多元文化教育,导致教师和学生对移民具有偏见而产生敌意(Dimakos and Tasiopoulou, 2003)。从这些反例可以看出,年轻人对移民的态度可能受经济衰退、民族主义、学校教育等因素的影响而“一改常态”,不是对移民更加友好,而是对移民更加排斥。因此,必须要具体分析年轻世代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及其影响,才能真正理解他们对移民的态度。
其实,世代分析在社会学研究中早已被提出,强调要理解世代所经历的具体经济社会情境。曼海姆(Mannheim,1970)是最早关注世代效应并将它作为重要议题的社会学家。在他的论述中,出生世代相同的人在成长期经历的社会环境是相似的,他们的态度可能被这些环境所形塑,并在后续生命周期里相对稳定。英格尔哈特(Inglehart, 1971, 2015)也认为,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取决于他成年之前占主导的社会环境,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为价值观定型提供了基础。埃尔德(2002)的《大萧条的孩子们》是社会学领域较早关注出生世代群体的实证研究。通过对美国大萧条前后出生一代的追踪调查,作者发现,大萧条不仅影响研究对象童年时期的生活环境,还影响他们成年后的工作和生活经历,甚至塑造了战后美国人注重家庭的价值观。海外学者对中国“上山下乡”青年的研究也揭示了共同经历对世代群体的心理和价值观的影响(周雪光、侯立仁,2003)。国内学者沈杰(2018)通过对世代理论的梳理,总结出塑造世代差异主要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等方面的影响因素,提出理解青年世代是理解代际与社会变迁的重要角度。
三、“世代—双城”比较:香港和上海的异同
对移民态度的研究开始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欧洲地区,近年来扩展至东亚地区(Shim and Lee, 2018)。国内学者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也刚刚起步,大多从经济利益或分层、文化认同或评价、群体威胁或接触等角度进行考察,并在研究发现或结论上有一定出入。例如,张雪筠(2008)对天津的研究和许涛(2012)对全国的研究都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对外地人更加宽容;李煜(2017)对上海的研究则发现用客观社会经济结构壁垒测量的“现实利益威胁假说”并未得到验证;梁玉成、刘河庆(2016)关于广州本地人对外国移民印象的研究证实了“群体威胁论”而否定了“群体接触效应”;许涛、王青青(2017)关于义乌市民对外籍人士社会距离的研究则表明,如果对外籍人士持有正面评价,那么增加社会交往的确可以显著拉近两个群体的社会距离。在这些少量研究中,只有田蕴祥(2015)关注了世代差异,发现“80后”和“90后”的年轻东莞居民对外来人口更多持中立或正面的态度。本研究沿着从欧美到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再到中国的路径,首次对香港和上海进行比较研究,考察两地居民对移民的态度在世代差异模式上是否存在异同,进而结合两地年轻世代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异同来理解。
这个“世代—双城”比较的研究设计与以往研究相比有两个重要优点。首先,已有研究大多用横截面数据分析单个社会,不管发现年轻人对移民更加友好还是更加排斥,都无法确认到底是否为世代效应。本研究虽然也使用横截面数据,但对比双城时,假定年龄效应具有普遍性(在所有社会的影响方向一致),如果两地年轻人态度模式不同,则证明很可能存在世代效应。此外,本研究在统计模型中同时纳入世代(分类变量)和年龄(连续变量)变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世代和年龄的共线性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世代和年龄效应(李骏、梁海祥,2020)。其次,已有理论或假设指出了宏观经济环境、个体经济利益、财政或福利负担、群体威胁或接触、地方和国家认同等重要解释因素,但多是分开讨论,而“世代—双城”比较可以将这些解释整合在一起。一方面,对世代效应的理解要同时考虑这些不同因素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对双城情境的比较又使这些不同因素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
对香港和上海进行双城比较还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与重要性。沪港都是移民城市,具有相似的经济社会发展史,经常被学界和公众进行比较。香港与上海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两个发展迅速的全球化大都市。香港岛于1841年开埠并根据《南京条约》割让给英国,上海则作为通商五口岸之一于1843年开埠,沪港两地从此成为中国与西方进行商业贸易等经济社会交往的两个窗口。香港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跃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上海则因为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而迎来三十多年的大发展。两个城市不仅在经济发展轨迹上相似,由于历史原因,在人口上也有诸多交融。然而,时至今日,香港与上海在相似的发展成就表面下,年轻世代却表现出不同的形象。上海的年轻人自信、开放、包容,香港的年轻人却成为反对内地游客等行动的主力。对此,媒体和公众已有所关注,但学界的相关研究却十分稀少。因此,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憾,围绕年轻人对移民的态度进行“世代—双城”比较。而要理解年轻人的态度,就必须要分析年轻人在两地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异同。
老一代香港人经历的是香港的经济腾飞时期,他们在个人收入、生活条件等方面都受益于宏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是,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年轻一代经历的是香港经济不振的时期,金融危机的冲击、发展红利的消耗、高昂的房价、文凭的贬值等都在不断挤压年轻人的生存发展空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香港年轻世代的初职收入持续下跌,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年轻世代的实际收入远远落后于年老世代。同时,年轻世代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是最高的,但他们从事低技能职业的比例相对于年老世代却不断攀升。1在上海,老一代经历的是80年代末下岗失业等各种阵痛,到了新一代出生成长时期,上海已经开始收获各种改革成果。两地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在GDP上的对比就非常明显:2007—2017年,香港的GDP增长率仅为61.3%,而上海的GDP增长率则高达151.3%。2当然,上海年轻人目前也像香港年轻人一样面临高房价的问题,老一代的住房等财富积累在代际传递的过程中,既为某些本地年轻人提供了更好的保障,也可能同时维持甚至扩大了财富的不平等(吴开泽,2019)。
在香港的社会福利制度下,移民只要通过合法身份进入香港超过六个月,就可以办理香港居民身份证,在享受社会福利方面与永久居民几乎不存在差异。因此,大量移民的迁入对包括年轻人在内的香港本地人客观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福利争夺。上海的福利制度情形有所不同,移民分为“事实上的”与“法律上的”两类。前者是指从外地到上海工作居住但没有获得上海户籍的流动人口,他们不享有上海为市民提供的各种福利和保障;后者是指获得了上海户籍的新市民,他们享有上海市民的福利保障待遇。当然,上海也在不断改革与户籍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自2002年开始实行致力于人才引进的居住证制度,2004年将居住证持有对象扩大到所有在本市居住的非本市户籍境内人员,他们可以享受包括义务教育、就业、医疗等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2009年又出台居住证转办户籍的新规定。但是,居住证和户籍所对应的市民福利待遇仍然存在不少差别,居住证转办户籍仍然相当困难(孔媛,2011)。因此,移民并没有被真正纳入与上海户籍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制度,本地人包括年轻人的社会福利始终受到政策保护。
两地青年的差异还体现在他们对地方和国家的认同上。新一代的香港青年土生土长于香港,从小与内地没有太多接触,“祖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香港回归之后的教育制度和内容也对他们的身份认同有深刻的影响。1998年,“公民教育科”成为中小学生的必修课。2001年,香港教育局又将“培养国民身份的认同”作为德育与公民教育的一部分。3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关于中国历史和国情的教育内容缺失,教师队伍良莠不齐以及对教材内容的解读不当,使得原本就较为宽泛的国民教育内容流于形式。大多数香港学生在中小学时期的国家认同教育是缺失的,而这个阶段恰恰是个人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李龙(2015)认为,香港人的国家认同存在两大不足,其中之一就是香港回归后国家认同教育内容的缺失。再加上香港的产业空心化、阶层固化和贫富悬殊,“本土派”随之崛起(魏南枝,2018)。研究显示,从2008年左右开始,“香港人”和“中国人”两种身份认同开始脱节,特别是2012年之后,香港年轻人的“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是呈显著上升趋势(Veg,2017)。有关调查也显示,香港青年的国民身份认同感2007年以后也大幅下降。4这反映了香港民众对本土身份认同的不断攀升和对国家认同的不断下降。特别是在香港年轻人中,本地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斥,许多年轻人认为自己只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反观上海,虽然也有地方认同,但与国家认同不存在分裂或互斥,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他们对自己是上海人与自己是中国人的认同是不矛盾的。
最后,两地公众舆论对移民的叙事倾向和话语建构也存在明显区别。在香港,对移民的叙事和话语由市场媒体主导,对移民的报道和评价往往比较负面,整体舆论环境对移民不友善,久而久之就营造出一种移民威胁的论调。近年来香港发生的“反双非”“反水客”等事件都不乏媒体的推波助澜。但在上海,对移民的整体舆论受到政府主导的宣传影响,主流观点是肯定移民或外来人口对城市建设和发展作出的贡献。近年来,政府更积极倡导用“新市民”取代“农民工”概念,以消弭民间社会对外来人口的歧视。这种正面、包容的舆论氛围对引导本地居民对移民的态度起到了积极作用,有调查表明,上海本地人对外地人,特别是对那些遵纪守法、为城市长期服务的劳动者,是持积极态度的(康岚,2015)。
综上所述,香港的宏观经济发展疲软,年轻人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受限,因国家认同教育缺失而使地方认同趋强,加之客观上移民对福利的竞争和舆论上媒体对移民威胁的放大,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可能使年轻世代对移民的态度更排斥。相反,上海的宏观经济增长动能强劲,年轻人享受改革红利,“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使其福利受到保护,户籍制度改革和主流舆论宣传又弱化了地方认同而强化了国家认同,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可能使年轻世代对移民的态度更友好。因此,在香港和上海,由于所处经济社会环境和自身特点的差异,年轻世代对移民的态度可能会出现鲜明的反差。
四、数据、变量与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于2017年完成的第一轮“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5和香港科技大学应用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于2017—2018年完成的第四轮“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HKPSSD)。6这两个调查项目在时间点上相近,都采用了概率抽样,都对两地的常住人口具有代表性。
本文研究的是上海和香港的本地居民对外来移民的态度,因此将两地的分析样本都限定为本地居民。对本地居民的定义,首先依据的是法理上的市民身份,在上海是指拥有上海户籍的人,在香港是指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人,因为上海户籍和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都是从法理上对两地市民权的界定,具有概念和逻辑上的一致性与可比性。但是,两地法理上的市民身份都可以通过先天和后天两种方式获得。因此,本研究还会将本地居民划分为本地出生和外地出生两个组别做进一步分析。
两地调查数据都使用社会距离量表测量人们对移民的态度,包括五个题项:“是否愿意和移民一起工作”“是否愿意移民居住在自己的社区”“是否愿意移民居住在自己的隔壁”“是否愿意邀请移民来自己的家里”“是否愿意自己的亲属或子女与移民谈恋爱”。在上海数据中,该量表的alpha信度系数为0.8,因子分析显示有且只有一个公因子,特征根为2.4,解释变异量为83.1%。在香港数据中,该量表的alpha系数为0.8,因子分析显示有且只有一个公因子,特征根为2.8,解释变异量为87.5%。将“不愿意”赋值为0,“愿意”赋值为1,五个题项得分相加即为对移民的态度,数值越大,表示越友好或越接纳。对于“移民”的具体措词和表述,在上海调查问卷中是“外地人(非上海本地人)”,在香港调查问卷中是“内地人”。7后者清晰地指向从内地到香港的移民,前者虽然从字面上看有些模糊,既包括从其他省市区到上海的移民,也包括从海外到上海的移民,但根据常识和口头表达习惯,调查员和受访者应该都是将其理解为从其他省市区到上海的移民。因此,两地调查数据中受访者对“移民”的想象大致都指向从内地来到本地的移民,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的关键自变量是“出生世代”,在两项数据中都划分为四组,依次是“1959年及以前出生”“1960—1969年出生”“1970—1979年出生”“1980年及以后出生”。用于解释世代差异的变量主要是三个:“教育程度”“生活满意度”“地方认同感”。教育程度既可用受教育年限来定序测量,也可用“是否接受了大学教育”来分类测量。生活满意度是个人对生活状况的总体评价,能够反映工作、收入和社会流动机会等多方面的影响。在本研究中,它是连续变量,依据生活满意度量表对五个题项的打分进行加总(每个题项均为1—7分),包括“我满意自己的生活”“到现在为止我能够得到我在生活上希望拥有的重要东西”“我的生活大致符合我的理想”“我的生活状况相当圆满”“如果我能重新生活差不多没有什么东西我想改变”。在上海数据中,该量表的alpha信度系数为0.8,因子分析显示有且只有一个公因子,特征根为2.6,解释变异量为95.1%。在香港数据中,该量表的alpha信度系数为0.9,因子分析显示有且只有一个公因子,特征根为3.0,解释变异量为94.9%。地方认同感是定距变量,两地调查分别询问受访者对“上海人”或“香港人”的认同程度,从“非常不认同”到“非常认同”依次赋值为1—7分。遗憾的是,这个变量在上海数据中只询问了移民而没有询问本地人,因此,对上海将只在分析外地出生样本时才会使用此变量。除以上变量外,数据分析还将控制“年龄”、“性别”(“男性”=1)、“婚姻状况”(“已婚”=1)、“工作状况”(“工作”=1)、“与移民接触程度”等变量。“与移民接触程度”变量,在上海调查数据中只询问了工作者中的雇员群体,仅分析这部分群体会导致样本大量删失,因而无法使用。但在香港调查数据中询问了所有受访者,因而可以使用,题目是“您在香港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与内地人的接触频率怎样”,选项从“从未接触”到“非常频繁地接触”共五个等级。
本文第三部分论述了上海和香港年轻世代身处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以及两地青年在社会认同上具备的特点。对此,可以用两地调查数据来进行描述比较。表 1列出了两地每个世代的受教育年限、生活满意度、地方认同的均值,对“70后”和“80后”还分别列出了“本地出生”和“外地出生”两组的均值。在两地,年轻世代的受教育年限都是最长的,但他们对生活机会的感受(用生活满意度来反映)是不同的。上海的“70后”和“80后”比较相像(全样本、本地出生组、外地出生组均是如此),生活满意度比老一代略低或相当。但香港的“70后”和“80后”差别很大(全样本、本地出生组、外地出生组均是如此),“70后”的生活满意度略高或相当于老一代,“80后”的生活满意度却略低于老一代。我们在对香港的补充数据分析后发现,在各个世代中,“70后”在失业率、管理/专业人员比例、工资中位数上都最好,但“80后”的失业率最高,管理/专业人员比例比“70后”低11.2%,工资中位数也低于“70后”,这可能就是导致他们生活满意度一高一低的原因。再来看地方认同,上海(数据仅限于外地出生样本)的“70后”和“80后”仍然比较相像,地方认同都比老一代更低。但香港的“70后”和“80后”仍然有所差别,“70后”的地方认同只是略高于老一代(外地出生组甚至比老一代略低),但“80后”的地方认同明显高出许多(外地出生组也是如此)。综上所述,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尽管年轻世代都获得了更高的教育,但生活满意度和地方认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上文对两地年轻世代所处生活发展环境差异性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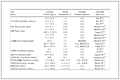
表 1 世代差异(自变量)
五、数据分析与结果
我们先通过双变量分析来初步考察上海和香港两地不同世代对移民态度的差异(见表 2)。在上海,“80后”对移民的态度最友好,在工作、居住、到访、恋爱等方面都表示“愿意”的占比在各世代中最高,达到66.6%;相应地,均值也最高,为4.4。“70后”与“80后”十分相近,在各方面都表示“愿意”的占比为61.1%,均值也为4.4。我们进一步把上海的年轻世代分为本地出生和外地出生两组,发现他们对移民的态度都比老一代更友好。以“80后”为例,本地出生组愿意在各方面都接纳移民的占比为63.0%,均值为4.4;外地出生组的占比更高达85.6%,均值也高达4.8。“70后”中的本地出生组和外地出生组同样如此,虽然相应数字比“80后”略低。这表明,上海的年轻世代对移民的态度更友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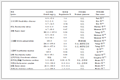
表 2 世代差异(因变量)
在香港却完全是另一种相反的图景,“80后”年轻世代对移民的态度最排斥。他们在五个方面均持接纳态度的占比仅为44.8%(在各个世代中最低),在五个方面均持排斥态度的占比为8.4%(在各个世代中最高);相应地,他们的态度均值仅为3.6,在各个世代中也最低。我们进一步把香港的“80后”分为本地出生和外地出生两组,发现他们对移民的态度迥异。前者极端排斥,愿意在各方面都接纳移民的占比仅为38.9%,均值仅为3.4;后者则最为友好,相应数值分别为65.1%和4.3。此外,“70后”对移民的态度也更像老一代而不像“80后”,无论是在各方面都接纳移民的占比还是态度均值,他们都与1970年以前出生的世代十分接近。但是,“70后”也存在内部差异,本地出生组对移民的态度比老一代较为消极,外地出生组的态度却更加积极。可见,香港区别于上海的另一个特点是,年轻世代对移民态度存在巨大的内部差异,极端排斥态度由本地出生的“80后”群体所主导。
接下来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回归模型来确认,在多元统计模型中,本地居民对移民态度的世代差异在上海与香港是否仍然有所不同以及如何不同。8表 3左栏是上海数据的分析结果。模型1显示,在控制有关变量后,与参照组“60前”出生世代相比,“70后”和“80后”对移民持更加接纳的态度(回归系数为正向显著)。模型2在加入“年龄”变量后,仍然发现“70后”和“80后”对移民的态度更积极,相应的回归系数甚至变得更大了。模型3在加入“是否本地出生”变量后,结果仍然如此,只是回归系数有所减小。可见,上海的年轻世代确实整体一致地表现出对移民更加友好。表 3右栏是香港数据的分析结果。控制有关变量的模型1显示,“70后”对移民的态度与参照组没有显著差异(回归系数不显著),“80后”的态度确实比参照组更消极(回归系数为负向显著)。模型2和模型3在递进控制年龄和“是否本地出生”变量后,结果仍然如此,相应的回归系数甚至不断增大。可见,香港以“80后”为代表的年轻世代确实对移民更不友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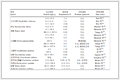
表 3 世代差异的OLS模型结果
此外,不管是在上海还是香港,本地出生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向显著,这意味着法理意义上的本地居民内部确实还存在文化或社会意义上的区别,土生土长的“老上海人”比异地来沪的“新上海人”更排斥移民,香港出生的“本土派”也比内地到港的“新移民”更排斥移民,这也印证了“群体威胁论”。
接下来,我们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通过设定“世代→教育/生活满意度/地方认同→对移民态度”的中介作用路径,在控制相关变量的情况下,考察世代之间对移民态度的差异是否与他们在教育、生活满意度、地方认同上的差异以及这些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有关。在SEM模型中将对有关变量作简化处理:首先,由于模型估计要求所有变量均为连续或虚拟变量,所以将世代简化为“年轻世代”与“其他世代”两组进行比较,在上海数据中将“70后”和“80后”合并为“年轻世代”,在香港数据中将“80后”界定为“年轻世代”,因为上文从表 1到表 3都已经显示,在上海,“70后”和“80后”更相似,而在香港,“70后”与年老世代更相似;其次,为突出大学教育的重要性,直接使用“是否接受了大学教育”这个虚拟变量。此外,由于上文从表 1到表 3也已经显示本地出生组与外地出生组的明显区别,这里将对两组样本分别估计SEM模型。
表 4是对本地出生样本的SEM模型结果。左栏上海的分析结果显示,年轻世代的大学教育机会和生活满意度都显著更高,在控制这两个变量后,对移民态度的直接效应(系数为0.302)正向显著,通过这两个变量对移民态度的间接效应(系数为0.121)也正向显著,其中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28.6%。大学教育、生活满意度与对移民态度之间的关系与理论预期一致,是正向显著的。这说明,“世代→教育/生活满意度→对移民态度”的作用路径是成立的,并且这个中介效应所占比例还不低。

表 4 世代差异及其解释的SEM模型结果(本地出生样本)
表 4右栏香港的分析结果显示,年轻世代的大学教育机会显著更高,生活满意度更高但不显著,地方认同显著更高,在控制这三个变量后,对移民态度的直接效应(系数为0.059)并不显著且为正向,通过这三个变量对移民态度的间接效应(系数为-0.215)为负向显著。同时,大学教育对移民态度的影响虽然正向但不显著,生活满意度对移民态度的影响正向显著,地方认同对移民态度的影响如理论预期的那样负向显著。这说明,“世代→教育→对移民态度”的作用路径只在“世代→教育”这个前半段而未在“教育→对移民态度”这个后半段成立;“世代→生活满意度→对移民态度”的作用路径未在“世代→生活满意度”这个前半段而只在“生活满意度→对移民态度”这个后半段成立;只有“世代→地方认同→对移民态度”的作用路径在前后两段都成立,也因此主导了世代的整个间接效应甚至总效应。
表 5是对外地出生样本的SEM模型结果。左栏上海的分析结果显示,年轻世代的大学教育机会显著更高,但由于大学教育对移民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导致“世代→教育→对移民态度”的作用路径不完整。年轻世代的生活满意度较低但不显著,地方认同较高但不显著,所以,尽管生活满意度和地方认同对移民态度的影响显著且符合理论预期,“世代→生活满意度/地方认同→对移民态度”的作用路径也不完整。因此,“世代→教育/生活满意度/地方认同→对移民态度”的整体作用路径不成立,年轻世代对移民态度的间接效应(系数为0.009)为正向不显著。此外,年轻世代对移民态度的直接效应(系数为0.249)是正向边缘显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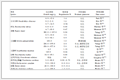
表 5 世代差异及其解释的SEM模型结果(外地出生样本)
表 5右栏香港的分析结果显示,年轻世代的大学教育机会显著更高,但大学教育对移民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导致“世代→教育→对移民态度”的作用路径不完整。年轻世代的生活满意度显著更低,地方认同显著更高,加上这两个变量对移民态度的影响也是显著并符合理论预期的,所以“世代→生活满意度/地方认同→对移民态度”的作用路径是成立的,它也因而主导了“世代→教育/生活满意度/地方认同→对移民态度”的整体作用路径或间接效应(系数为-0.128)的方向和显著性。此外,年轻世代对移民态度的直接效应(系数为-0.123)是不显著的。
总之,表 4和表 5呈现的年轻世代对移民态度的间接效应模式实质上都取决于他们与解释变量(教育、生活满意度、地方认同)之间以及解释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式。表 4和表 5还反映了,不管是在上海还是在香港,教育、生活满意度、地方认同与对移民态度的关系是相当一致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为正向显著,意味着生活满意度越高,对移民的态度就越友好。地方认同的影响为负向显著,意味着地方认同越强,对移民的态度就越排斥。因此,经济利益和社会认同两大理论都得到印证。大学教育的影响在上海本地出生样本中为正向显著,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确实会使人们在价值观念和社会态度上更加开放、自由和包容。但它在香港的两组样本中以及在上海的外地出生样本中虽然为正向并不显著,具体原因还有待深入研究。此外,在表 4和表 5香港数据的模型中,移民接触变量对移民态度的影响都是正向显著的,这表明接触可以消解群体刻板印象,改善群际关系,印证和支持了“群体接触论”。
六、总结与讨论
年轻人对移民更友好吗?已有对移民态度的研究忽视了世代这个重要的分析视角。虽然一些研究在模型中控制了年龄或出生组变量并发现年轻人对移民态度更友好,提出了若干解释,但没有区分是年龄效应还是世代效应。另一些研究甚至有相反的发现,这给世代效应的本质或方向问题打上了问号,提示必须要具体分析年轻世代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及其影响,才能真正理解他们对移民的态度。
基于此,本文沿着该领域从欧美、东亚再到中国的路径,首次对香港和上海进行“世代—双城”比较研究,并整合验证已有文献提出的宏观经济环境、个体经济利益、财政或福利负担、群体威胁或接触、地方和国家认同等重要理论解释。通过分析年轻世代在两地所处经济社会环境和自身特点的差异,本文认为,香港和上海的年轻人对移民的态度可能有鲜明反差。香港的宏观经济发展疲软,年轻人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严重受限,年轻人因国家认同教育缺失而使地方认同趋强,加之客观上移民对福利的竞争和舆论上媒体对移民威胁的放大,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可能使年轻世代对移民的态度更加排斥。相反,上海的宏观经济增长动能强劲,年轻人享受到了改革红利,“二元”保障制度使其福利受到保护,户籍制度改革和主流舆论宣传又弱化了地方认同而强化了国家认同,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可能使年轻世代对移民的态度更友好。
通过分析第一轮“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和第四轮“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HKPSSD)这两项在调查时点、抽样设计和变量设置等方面都具有高度相似性的数据,考察本地居民(包括“本地出生”和“外地出生”两个组别)对移民态度的世代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如何受到教育程度、生活满意度、地方认同感这三个主要解释变量的影响,本文呈现并证实了上述理论分析和预期。
首先,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年轻世代的教育程度都是最高的,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地方认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上海的“70后”和“80后”比较相像,生活满意度比老一代略低或相当,地方认同感更低。然而,香港的“70后”和“80后”差别很大,“70后”的生活满意度略高或相当于老一代,“80后”的生活满意度却略低于老一代;“70后”的地方认同只是略高于老一代,但“80后”的地方认同明显高出许多。
其次,上海和香港的年轻世代对移民的态度确实迥异。上海的年轻世代,不管是“70后”还是“80后”,也不管是本地出生还是外地出生,都整体一致地表现出对移民更加友好的态度。香港的年轻世代却因出生背景不同而存在内部态度分裂,本地出生者对移民更排斥,外地出生者对移民更友好;反映在总体上,“80后”的态度显著更消极,“70后”的态度更像老一代而不像“80后”;香港年轻世代对移民的极端排斥态度由本地出生的“80后”群体所主导。
再次,通过设定并检验“世代→教育/生活满意度/地方认同→对移民态度”的中介作用路径发现,年轻世代对移民态度的间接效应模式确实取决于他们与解释变量(教育、生活满意度、地方认同)之间以及解释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模式。简而言之,年轻世代的教育程度更高,生活满意度分化,地方认同高低与他们对移民的友好或排斥态度强弱有密切的内在关系,最终导致上海和香港本地居民对移民的态度表现为截然不同的世代差异模式。如果要比较世代差异经由这三个主要变量影响对移民态度的中介路径或间接效应的话,在上海是教育和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更强,在香港则是地方认同的中介作用更强。
最后,几个解释变量本身对移民态度的影响也印证了已有文献提出的几个主要理论,并且是同时适用于沪港两地的。个体生活满意度越高,对移民的态度就越友好,印证了“经济利益论”;个体地方认同感越强,对移民的态度就越排斥,印证了“社会认同论”;本地出生组比非本地出生组对移民的态度更排斥,印证了“群体威胁论”;与移民接触越频繁的个体对移民的态度越包容,印证了“群体接触理论”;对年轻世代态度更加开放的“教育解释论”在上海本地出生样本中得到印证,在香港本地出生和外地出生样本中虽有此迹象但未得到印证,结合本文对香港教育问题的讨论和已有研究对希腊教育问题的类似发现,表明了教育对价值观念的影响到底如何取决于教育体系的实际运作过程和内容。因此,如果要引导与调和本地居民对外来移民的负面态度,就需要从经济发展与利益分配、抑制地方认同与培育双重认同、提高教育程度并真正传递开放包容价值观等方面同时入手。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杂志,2021, Vol. 41 ›› Issue (5): 180-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