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
坛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人类学解读
提要:本文尝试揭示位于川青交界的果洛和色达如何在19世纪成为藏族眼中代表佛教宇宙的坛城。除了呼应当代人类学对“地方”概念的重构,这个发现还能证明这片历史上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牧区曾存在一个从文明边缘成长为中心的想象。费孝通在论及藏彝走廊时有“一子相连,全盘皆活”的期许,挖掘藏区边缘坛城宇宙观的历史有助于实现这个愿景,与东南亚人类学的比较则可为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表征提供一个人类学解读。
关键词:坛城;藏传佛教中国化;藏彝走廊;佛教人类学
作者简介:李晋(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助理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国内人文学界对历史上的汉藏佛教互动已经做出细致的梳理,以呼应党中央新近提出的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论述(沈卫荣,2022)。本文把目光投向汉藏佛教纽带在今天的枢纽——位于川青交界的果洛和色达。这两片牧区在过去曾经是清朝官员和民国知识分子慨叹的政权未及完善之地,也是西方探险家未能进入的“亚洲最未知的角落”。中国学界习惯用汉藏文明的“边缘”来形容历史上的安多和康区,地处安、康交界的果洛和色达在这个框架下可以算是“边缘的边缘”。这个边缘地带之所以在今天成为汉藏佛教互动的枢纽,是因为它们早在19世纪就被认定为一个有待崛起的佛教的中心。本文尝试从这个边缘地带的中心观中发现论述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线索。
更具体地讲,本文关注的是“坛城”这个佛教用以解释文明中心和边缘的图式。在梵文里,“坛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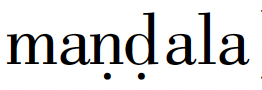
我在调查中发现,最能证明果洛和色达是一个有待崛起的佛教中心的表征是它们从19世纪起就被描述为坛城。这个坛城话语背后是一个更加漫长的坛城图式从印度传播到卫藏,并逐渐传播到康区和康区边缘的过程。考虑到果洛和色达对汉藏佛教纽带的推动,这个坛城图式的迁移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因为不管“中国化”的面相如何复杂,至少在空间轨迹上,这个自西向东的移动过程证明,藏族世界对佛教中心的定位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群体眼中经历过一个不断远离印度并越来越接近青藏高原东缘和汉地的过程。研究坛城图式在青藏高原上的变化有可能为论述藏传佛教中国化开辟新的角度,并证明人类学对这一领域的意义。作为初步尝试,本文希望在理论上给出一些不同于东南亚研究的阐释藏地坛城的框架。我希望在此基础上说明,当果洛和色达不再是地图上的边疆,而是位于中央的坛城,历史上的“蛮夷”不再是西方考察者眼中阻碍考察的牧民,而是这些考察者自身——牧民们用暴力阻碍这些考察者进入他们的领地,是在以护法身份保卫坛城免受魔军的侵扰。通过揭示历史能动者如何在佛魔争斗的主题下获得形象,本文尝试在每个社区定义自己的路径中发现被遮蔽的知识。
二、转向坛城之外:剧场国家、星团政体与佛教坛城观的异同
果洛和色达彰显了坛城政体是个融合自然、宗教和政治的“宇宙政体”(cosmic polity)。以色达为例,这里的大头人骨系有六个村庄和一个家庙,占据“色塘”(意思是“金草原”)这个全境的中心。这个中央区域又进一步以珠日莫波这个全境最高的神山为中心。这样,整个地景模仿了佛教的须弥山和山脚下的金轮,它意味着色达是一座等同于佛教宇宙的坛城,境内的所有自然要素(比如日月星辰和山川河流)和六道众生(僧俗人畜、飞禽走兽和看不见的鬼怪与神明)共享了坛城的神圣。在色塘外围,有四个更小的联盟骨系拱卫着色塘(色达政协编写小组,1997:35),形成坛城最基本的“一城四门”的结构——中间是代表宗教和政治中心的内核,四周有模仿它的属地。在东南亚,同样的模式可以用来组织以世袭群和村落为基础的刀耕火种的农业社会,以及军事和政治层级都较为发达的集权王国;它们可以用作建筑和城市布局,也可以用作官僚体系的层级结构。这个“一城四门”的结构可以进一步扩展成九个(在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各添加一个附属部分)、三十三个(形成几层的同心圆)或包含其他数目单位的向心政体,移植“五方佛”“九方佛”“三十三天”等佛教对宇宙秩序的描绘(Tambiah,2003/1973)。它表示整个地区的社会和政治形态在佛教化过程中发展出契合佛教的形态。
涂尔干对图腾制度的讨论是人类学讨论宇宙政体的原型。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里,涂尔干解释了一个叫“储灵珈”(churinga)的圣物如何在澳大利亚图腾仪式中占据中心,让周围的氏族成员和动植物在其辐射下拥有免于伤痛的能力,并与更外围依旧处于世俗状态的事物形成区分(Durkheim,1995/1912:118-126)。格尔茨和坦拜亚移植了这个框架。在格尔茨论述的巴厘,每个政治—礼仪中心通过典礼仪式在统治区域建构出“尼加拉”(negara)与“德萨”(desa)的对立:尼加拉代表皇宫、国都、市镇、国家、文明等神圣的部分,德萨代表郊野、村庄、属国、地方、世界等可以被前者改造的部分(Geertz,1981)。如果把这里的政治—礼仪中心比作储灵伽,那么格尔茨和坦拜亚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们在涂尔干的模板下添加了等级和更多的中心:位于最高点的君主拥有最神圣也最接近宇宙的地位,其他地方中心在模仿他的同时缩减了典礼的排场和规模。与储灵珈仅仅在水平方向上辐射不同,在东南亚坛城政体的每个垂直层级上都有与之对应的政治和礼仪中心,并建立了一个向心但逐层递减的等级秩序。每个大的坛城在自己的边缘包含很多小的坛城,后者在依附和模仿坛城中心的过程中推动整个图式向边缘地带复制。
“剧场国家”和“星团政体”这样的偏正短语突出了宇宙政体作为政体的一面,但是这个结合宗教与政治的神圣中心实际上需要更细致的辨析。至少在藏地,作为宗教领导者的僧团往往强调他们与作为世俗领导者的土司和头人之间对坛城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些修行者强调王权追求的是延续与恒常,但再辉煌的坛城都要符合“无常”这个设定。
佛经中用来解释坛城形成的“降魔成道”的故事表达了这个观点。按照《佛本行集经》的描述,当时还未成佛的悉达多太子(称作“菩萨”)在金刚座上进入禅定,发誓要找到跳出轮回的方法。这惹恼了把众生禁锢于轮回的魔王。魔王波旬召集夜叉、罗刹、毕舍遮、鸠盘茶等百千万亿鬼众“閦塞填噎菩提树前……欲杀菩萨”。悉达多用右手指地,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尔时彼魔一切军众及魔波旬……皆悉退散”(《佛本行集经》卷二十七至二十九)。证悟后的悉达多以金刚座为中心,创立了一座包含日月、莲花、须弥山、铁围山、大海、虚空、地水火风等宇宙要素在内的坛城。由波旬长子领衔的魔众在当晚就皈依为佛的弟子,成为最早进入坛城的众生。这个坛城的边界随着佛陀游历诸国、广摄弟子而扩大。佛传故事有意点出这个坛城不等同于神圣王权创造的坛城。波旬在发动攻击前诱惑佛陀,说只要放弃成佛就可以成为所有人都“渴仰”的圣王,佛的回答是再伟大的君主都因为不懂得无常而受到轮回的控制,他创造的坛城要教会人们理解无常(《佛本行集经》卷二十八)。佛教强调一个个具体的坛城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迟早会消失。
这样一种意识意味着我们必须打破涂尔干为格尔茨和坦拜亚设定的模板。涂尔干在研究仪式时强调“社会”的先在地位。他认为宗教宇宙观是社会的集体表述,宗教感染力是集体行动对个体的共振。在他看来,氏族成员用代表氏族的花纹装饰储灵珈表面和自己身体表面的事实足以证明,那个通过道德敬畏感来控制个体的“神圣世界”就是社会。这套方式为宗教制造“社会”这个后景(ground)的同时,也制造出某种循环阐释的效果,它需要我们在一个设定好的社会范畴内解释作为其显现的宗教如何塑造其自身。与此类似,坦拜亚和格尔茨在讨论坛城时给定了观察的后景和边界。格尔茨强调宇宙观和典礼等想象性能量如何实现坛城中心对边缘的绑定,坦拜亚则把这个绑缚关系归因为文化、政治、经济和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但是在讨论中心对边缘的框定时,他们总是预先设定好了那个他们想要回答的坛城政体的边界,在一个已经给定好的坛城内回答它是如何存在的。
这套路径最重要的弱点在于,它没能解释坛城之外的世界对它有何种意义。格尔茨从没真正讨论过荷兰殖民者和伊斯兰爪哇这两个他一带而过的他者,但是威尼差恭的研究让我们看到越南和缅甸这两个被想象为魔军的他者对暹罗这个星团政体的确立有着重要意义(Winichakul,1994:7、35)。伊利亚德早已指出,保护神圣空间免于外来世俗事物的闯入是维持“圣俗二分”的关键(Eliade,1987:29-65),涂尔干自己也提到不能有氏族之外的成员触碰储灵珈是图腾仪式的要求之一(Durkheim,1995/1912:119)。12世纪之后的佛教徒在望向中心时只看到佛陀的圆寂和印度佛教的消亡,如果想要仿效已经消失的中心,他们必须像佛陀那样去“伏魔”——到一些从未有坛城覆盖的边缘地区(这种从未受佛教影响的地区在佛教里被污名化为“魔境”和“蛮夷”)摄受众生并创立新的坛城。相比于格尔茨和坦拜亚把目光投向坛城内部和中心,佛教世界更关注已有坛城与更遥远世界的关系。不同于东南亚人类学关注某一坛城在众星捧月状态下的延续,强调无常的佛教徒更愿意突出佛教社区的起落和新老坛城的交替与位移。
这意味着我们应该用更细致的态度反思项飚对坛城政体(他用的是“曼荼罗”)的论述。在他的文章里,通过比较坛城和儒家天下观,项飚强调“在国族成为主要的政治单位之前,以自我为中心、由内而外、无限延伸的空间想象可能是相对普遍的”(项飚,2009:105)。在某种程度上,坛城被定义为一个能无限延展的神圣空间是坛城外围往往遭到忽略的原因,因为“无边界”的设定似乎意味着“边界之外”是无需考虑的后景。如项飚所言:
在曼荼罗政体中,掌握神权的统治者居于中央,他对社会控制程度,社会对他的忠诚程度,以及地方社会的文明程度,都从中心到边缘逐步稀释。在这一政体中,中心是绝对明确的,边缘地带是模糊的,现代意义上的“边界线”是不存在的。(项飚,2009:105)
项飚所说的“现代意义上”的边界应该指一条清晰的能够区分坛城内外的边界。不难想象,就算这样一条内外分明的边界不是坛城在理论上的特点,它也是一个坛城社区经常面对的现实。探索外部世界对坛城的塑造需要我们把项飚的论断重新加工成问题——当现实中确实存在对他者的感知,坛城内部该如何处理和表述这样一条本不该存在的边界?作为佛教徒的回答,“降魔成道”意味着众生在成佛和入魔之间处于两可状态,这种两义性对应项飚所说的坛城边缘的模糊性,它意味着在边界两端存在转化的可能,佛传故事强调即使是最凶悍的魔军也可能像波旬长子那样被降伏为佛的弟子。大卫·帕金(David Parkin)说一个文化看待邪恶的方式展现了它对世界本体和人之能动性的看法(Parkin,1985:6)。对应无常这个本体,佛教有跨越边界去度化众生的大乘伦理。星团政体和剧场国家通过周期性地回到中心来消除边缘的两义性,而不断拓展的佛魔交战则在前沿地带形成可移动的边界。佛教坛城需要研究者在边缘地带打开观察的边界,在持续变化的后景中把宗教放回到社会。当我们面对色达和果洛的坛城地景时,一个更符合佛教设定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向心地景是如何通过跨边界的移动从起源地传到藏区东缘的。不同于涂尔干把预设的“社会”当作分析的前提和起点,在处理坛城时,我们需要从人类学超越涂尔干的努力中寻找超越“地方”(locality)的方法。
三、探究坛城图式移动的理论路径
人类学从一个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社区关系来理解地方象征体系的习惯要追溯到涂尔干对功能主义的影响。在以拉德克里夫-布朗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里,人类学对调查边界的设定与涂尔干对理论边界的设定结合起来,让带有“地方”色彩的空间像涂尔干的“社会”那样被当作先验性的后景(Asad,1973)。小到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村落或社区,大到以单一国家、民族或语言为基础的地理共同体,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人类学都是以这样一些内部同质且与外部割裂的“地方”为代表性的后景(Wolf,1982)。70年代之后的人类学开始反思这门学科中一些看似客观的认识是否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和知识建构的结果(Clifford & Marcus,1986;Rosaldo,1989)。在这个过程中,带有“地方”色彩的空间框架成为反思的重点。80年代的人类学相信即使是最真实的“田野”(the field)也是田野调查者通过身体实践、书写策略和空间意识制造的产物(Gupta & Ferguson,1997;Candea,2007)。在这些反思中,一些学者开始用更精细的方式处理理论的后景。
为呼应这些进展,本文在概括坛城图式的流动时坚持三个方向。首先,不管是呼应全球化理论(Tsing,2000;Collier & Ong,2005),还是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把世界割裂成互不相交的模块(Fabian,1983;Wolf,1982),人类学替换涂尔干框架的方式之一是把文化放在跨地方的视角下处理。借鉴这个视角,本文从移动、旅行、遭遇等更具流动性的意象中发现线路的意义(Clifford,1997),在关联性的位置网络中聚焦于不断变动的场所(Marcus,1995)。在每个这样的场所,佛教神话总是把坛城社区的诞生追溯到跨界的伏魔活动,说明历史上的佛教团体是在开辟更遥远世界的努力中才在普拉特所说的“接触地带”延展对坛城的想象(Pratt,1992)。文化不是在人群流动中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个地方,而是在流动过程中生成。
其次,正像“伏魔”是个充满权力和污名化关系的意象,佛教是通过对边缘地区的规训才把坛城建构为主导性的地景。不管我们把“地景”定义为“文化图象”(Cosgrove,1984)、“看待大地的方式”(Daniels,1985:151),还是“实践图式”(Bourdieu,1977),这些定义方式都说明地景需要一代代人在视线上的积累。作为通常所说的场所塑造(place-making)过程的结果,地景离不开在时空网络中切割地区边界和深度的时空地域化的过程,也离不开教会当地人用特定方式表达对大地体验的主体地域化的过程。在这个意识形态确立的过程里,地方知识生产、话语生产以及与权力和规训绑定在一起的主体问题是几个必不可少的面相(Appadurai,1996:178-182;Munn,1970)。
具体到我们的故事,伏魔仪式是让相关话语和观念演变为主体意识的手段。佛教徒相信在边缘地区表演这个仪式能圆满一个地区传播佛教并建立坛城的契机。在这些表演里,一个修行者把金刚橛插进波旬人偶的身体,钉在场地的正中。与此同时,他在脑海中观想出一个承载神明的坛城,并暂时获得与神明等同的力量。金刚橛在刺入大地时刺动着围观者的心弦,他们知道仪式表演者正利用仪式力量降伏鬼神和对手,并以现在金刚橛的位置打造出一个佛教认为会成为现实的坛城。这个仪式让围观者看到自己处在魔军被纳入坛城的位置——也就是现实中把边缘者和反抗者转化为皈依者的位置。如同涂尔干笔下的仪式一样,伏魔仪式把宇宙观转化成社会性的话语和体验,调伏了观看者的视线并塑造出佛教徒的集体意识和认同,仿佛有某种宇宙力量把社区成员打造成社会期待的样子。但这个过程不像涂尔干强调的那样仅仅建构出“社会”这个权威,仪式在塑造人地情感时塑造了寺庙团体相对于其他社会团体的等级关系,地景在承载人的体验和辨识时亦展示了权力与知识的共谋。
最后一个需要考虑的是仪式和地景的辩证关系如何存在于历史(Sahlins,1985;Dirks,1996)。可以想见的是这套辩证关系需要佛教团体的大量诠释才能在具体情境下调动,相关符号劳作(semiotic labor)是藏传佛教内部大量存在伏魔神话并用它们解释边缘地带崛起的原因。接下来的几节将呈现这些神话展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从西向东的轨迹,伏魔话语在先后塑造卫藏和康区后,又塑造了康区边缘的果洛和色达。拉图尔在批判涂尔干时提出了“重组社会”的主张。在他看来,涂尔干的“社会”应该被重新理解成人事词物等不同行动元(actants)在重要话语时刻的“聚合”(assembly)(Latour,2006)。与此类似,当本文不再把色达和果洛的坛城地景归结为某个预先存在的“地方”时,我们也有机会在藏传佛教发展、国家边疆建设和西方博物学事业的网络中追溯那些让果洛和色达获得坛城形态的节点(nodes)。
四、边地、伏魔与坛城
公元10世纪,当藏族求法者用“中心”(




很多藏传佛教神话都是顺着这个自我妖魔化的思路解释佛教或某个特定的密法派别在青藏高原上的崛起。一些神话甚至把真实的历史人物描述成从印度和其他佛教地区前来伏魔的菩萨。12世纪的拉萨密法团体创造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神话,神话创作者说释迦牟尼在圆寂前找到观音,让他在印度佛教衰败时到北边的蛮夷之地(藏地)创立一个受佛教指引的民族。神话接下来讲述了观音如何以石猴模样与藏地的罗刹女结合,创造出藏族最早的六个先祖(代表藏族六个古老的氏族)。当叙事进入8世纪的吐蕃王朝,神话创作者把藏王松赞干布描述为观音的化身,把他迎娶的唐朝和尼泊尔公主解释成观音幻化的度母。在高潮部分,读者能看到这个建构是为了把藏地佛教网络的产生解释成由观音主导的伏魔工作的完成。
在这个部分,神话着重介绍了吐蕃朝廷为唐朝和尼泊尔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佛像修建寺庙。起初,建庙工作进展得很不顺利,唐朝公主用堪舆术发现藏地的风水是个仰卧的罗刹女。这个不吉祥的风水导致白天修好的寺庙在夜晚被毁去。为了改造这个地景,松赞干布把戒指扔向拉萨卧塘湖的湖面,戒指入水的位置升起佛像,松赞干布指示藏人在佛像升起的地方填湖修建了大昭寺。这段情节有一个隐含的层面:卧塘湖对应罗刹女的心脏,与金刚橛刺入波旬人偶一样,在这个位置修建寺庙是在影射伏魔仪式对魔军心识的慑服。吐蕃朝廷以四座寺庙为一圈,在罗刹女身上又修建了十二座寺庙,每一座都是对最中心的大昭寺的模仿。最内圈的“镇茹寺”修建在罗刹女的肩膀和胯部,第二圈的“镇边寺”修建在肘部和膝盖,最外围的“再镇寺”修建在双手和双脚,像十二把金刚橛,这些寺庙把罗刹女牢牢钉在地上。
12世纪之后,这个神话由于藏族史书的反复援引而获得各教派都认可的正史地位。需要强调的是,两位公主为藏地带来的是释迦牟尼等身像,供奉这尊佛像的大昭寺与其他十二座寺庙以三重同心圆的方式镇住罗刹女的身体,在印度坛城的边缘位置复制出一座与它等同的坛城,这个坛城刚好覆盖住了与青藏高原等同的罗刹女的身体。十三座寺庙又在各自位置重复了相同的模式,恰如星团政体或剧场国家把代表整体的同心圆复制到整体的各个部分。在神话形成的12世纪,藏地经历了寺庙的修建风潮,也见证了内亚伊斯兰势力对印度佛教的毁灭。显然,经历这些变化的藏族人不再把自己看作是坛城边缘的蛮夷之地,他们开始把自己摆放在佛教世界的正中,以拉萨为中心的坛城想象是佛教中国化在青藏高原实现的标志之一。
十三座寺庙由内到外,从中心扩展到边缘。历史上的藏地佛教徒必定曾在新开辟的土地上大量表演伏魔仪式并生产与之相关的话语,把原有的藏族生境规训成佛教的面貌。藏学家米勒注意到十三把金刚橛在钉住罗刹女身体的同时遗漏了头部和面部(Miller,1998:22)。这个依然能活动的区域在藏地的哪个地方?它是否下一个等待伏魔的空白?如果像米勒那样确定罗刹女的右手在安多的苏毗,左手在康区的木雅,按照一幅十分出名的唐卡形象绘制的头与手的位置,这个依然可以活动的区域对应果洛和色达。有趣的是,如果采取直译,“果洛”(

五、果洛和色达的罗刹形象
我们已经指出,藏族社会最早因吐蕃王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劫掠行为在周边佛教世界获得了罗刹的名声。随着青藏高原佛教化过程的完成,慈悲成为规训藏族社会成员的首要准则。藏族社会的尚武精神沦为佛教徒眼中最被贬抑的本土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被十三座寺庙镇住的罗刹女象征着被镇住的尚武精神——僧侣们认为只有抑制藏族社会对暴力的热衷,才能把所谓“蛮荒之地”打造为坛城。由此产生的逻辑是罗刹和坛城形象总是并生的,越是把热爱劫掠的罗刹之地打造为坛城,僧侣们就越能突出自己伏魔的成效。
从未有政权设治的果洛和色达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认为是劫匪横行的不法之地。历史上包裹这片地区的商道有三条,一条从康定经甘孜到玉树,一条从玉树到西宁,还有一条从西宁经松潘到康定。在最能保证长距离移动的夏草丰美的季节,两地牧民会埋伏在这三条商道上打劫往来的商客,他们有时候甚至会以部落为单位来袭击对手。按照一位果洛头人的说法,抢得的财物在过去要首先留一份给果洛的大头人做礼物。余下的赃物分两份,出枪、出马、出粮者得大份,其余人分小份。战利品中如果有马匹,在分配时要留给队伍的领头者(俄后保,1982:91-92)。
清朝史书里关于果洛和色达的记述全都是它们的劫掠活动。1721年和1743年,康熙和乾隆两次派兵赴果洛追缴赃物,西宁和四川官军以及青海蒙古兵在案件高发期还要到关口监视牧民的动向(《清实录》第六册:862、867;《清实录》第十一册:461、801)。四川官员在1754年之前保持着每年或者每三年到果洛宣化的传统,敦促大头人控制好自己的下属(《清实录》第十四册:1079)。类似案件在19世纪的《清实录》里大为减少,但这很可能只是由于朝廷减少了对边疆的关注。1909年,赵尔丰在改土归流后要求色达“永不劫掠”(傅嵩炑,1968/1911:72),民国报刊也报道这些“野番”袭击周边地区(重庆中国银行四川月报社,1937:302、330)。1950年,康区各县要求人民政府尽快在果洛和色达设治,在民族团结政策下减少因抢劫发生的治安和械斗案件(甘孜县委会,1951:110;乔志敏,1952:24-25)。
这些不受管教的牧民甚至有可能直接挑衅寺院,像罗刹神话那样呈现反抗僧团的面貌。1751年和1766年,果洛部落袭击了班禅使团以及从拉萨返回的蒙古诺彦活佛的队伍(《清实录》第十四册:188;《清实录》第十八册:1144)。1808年,利用西宁护卫队从四百人减少到二百人的机会,他们又袭击了一支返藏喇嘛的使团(《清实录》第三十册:658-659)。1814年,拉萨政府派年班堪布进京朝贺元旦,果洛人埋伏并袭击了福克精阿派往省界迎接的五十名蒙古兵和五十名玉树番兵,逼迫他请求班禅喇嘛派佃户兵丁协助并招募一百名蒙古兵来固防(《清实录》第三十一册:1027-1028)。1829年,五六百名果洛人在通天河袭击了一支由卫藏寺庙派遣的赴呼和浩特贸易的队伍,夺走二十驮经卷、佛像和衣物,导致北京白塔寺的一名喀尔沁转世灵童在袭击中丧生(《清实录》第三十五册:230)。1835年7月,在三千名果洛牧民的伏击下,进京朝贡的前后藏堪布队伍几乎失去了全部货物和贡品(《清实录》第三十六册:985-986)。
20世纪50年代,藏族学者南卡罗布在调查色达时收集到一首歌谣,歌谣以牧民口吻称赞这些色达人(俄洛人)“吾俄洛肉食(

当时,我正在等待(果洛头人)给我回信,活佛突然让我立刻准备(进入果洛)。他刚刚得知自己寺庙的一个人在从果洛返回时遭到了抢劫和杀害。寺庙决定派一支“诅咒团”来报复。60个僧人将要被派到那个犯了杀业的部落并代表寺庙实施诅咒。活佛认为如果我能和这支队伍一起,就可以最终进入那片禁区……稍后我听说被诅咒的部落到半路迎接前来诅咒的僧侣,甘愿赔偿人命以躲避邪恶的咒语。这些果洛人虽然很勇敢,但是他们也非常迷信。(Rock,1930:164)
实际上,就算这些牧民不总是遵从佛教的要求,他们对身为罗刹的标榜已经反映出他们接受了佛教安排的位置和形象,这是地方佛教化过程完成的结果。在上述史料涉及的18和19世纪,果洛和色达已经开始成长为藏区宁玛派的中心。它们的劫掠行径为坛城话语的建立提供了土壤,僧侣们把两地牧民描述成罗刹,本质上是为了把他们的家园描述成坛城。在下一节,我将简要介绍曾经影响卫藏的坛城话语如何传播到康区和这两个更边缘的角落。
六、坛城话语在果洛和色达的形成
要理解坛城图式如何在从印度到卫藏的变化中进一步扩展到康区和果洛—色达这个青藏高原的东缘,我们必须首先说明康区佛教在18世纪的变化。在那个世纪,随着四川在军事、税收和行政上被清王朝打造成对抗准噶尔蒙古的前线(Dai,2009),一条联结四川和卫藏的商道为康区带来了建庙的财富和资本。18世纪中后期,经过俺答汗、固始汗和明清统治者的扶持,格鲁派在康区主干道上建立起一些颇具规模的寺庙;德格土司也为噶举派和萨迦派建立起新的中心。由于受到准噶尔蒙古的迫害,大量宁玛派僧人逃离卫藏,在白玉和德格建立起宁玛六大寺里的四座。19世纪的利美运动让康区成长为可以媲美卫藏的佛教文明的中心。康巴人是藏族社会最勇武好斗的群体,康区之于卫藏就像曾经的卫藏之于印度一样是一个热衷暴力的蛮夷之地。“从边地到坛城”很快被用来解释这些变化和康区佛教的崛起。
在宁玛派里,我们能最明显地看到曾经被用来形容印度和卫藏关系的伏魔话语被用来形容卫藏和康区的关系。比如在莲师神话里,神话强调藏王赤松德赞从印度邀请到被称为“第二佛陀”的莲花生进藏来伏魔,仿照坛城样式创立桑耶寺和藏地最早的僧团。接下来,它强调莲花生在离开卫藏前游历了康区的很多地方并降伏了当地的鬼神,他的25个弟子在未来的转世中会前往这些地点建立寺庙以推动康区佛教的发展。在上面的观音神话里,释迦牟尼委托弟子观音在未来的转世中降伏罗刹女以创立卫藏的坛城;在莲师神话里,类似的伏魔活动指引莲花生的弟子在未来的转世中推动康区佛教的发展。17世纪开始的卫藏佛教对康区的输入被整合进坛城宇宙观,康区佛教的崛起不但被描述成一个从边地到坛城的佛教的发展过程,而且被解释成“印度—卫藏”法脉的延续以及一个从印度到卫藏再到康区的坛城的迁移过程(Samuel,1993;Gardner,2006;Huber,2008:85-121)。
可以想象,这个宇宙观反过来会影响历史能动者的选择及其对社会和自然的卷入。在康区崛起的几个世纪里,很多宁玛派僧人到一些位置偏僻的莲花形状的山谷或是金刚橛形状的山峰建立修行场所或寺庙,声称这些具备坛城形态的地景是莲师伏魔留下的痕迹。这些宁玛派精英因为可以被奉为莲师25弟子的转世。借助这些所谓的伏魔地点和重新发现的“圣地”,宁玛派在康区拓展出广阔的密法传承网络和朝圣网络,把坛城图式逐渐推向边缘。
在果洛和色达,以多智钦寺和敦珠家族为核心的密法团体主导着两地的蜕变。一世多智钦在德格学成后受到卫藏政府和很多土司的赏识,被嘉庆皇帝册封为青海蒙古部落的上师。晚年的一世多智钦试图发展家乡的佛教——他认为阿尼玛卿和珠日莫波这两座神山是莲师伏魔后用金刚橛幻化的地橛(
七、坛城中的牧民:从魔军到护法
佛教的无常观意味着一座坛城迟早会毁灭,维护坛城安全成为恒久的主题。威胁坛城的力量大多来自外围——不信仰佛教的异族和其他世俗势力占据的需要伏魔的位置。正像魔王在佛经中驱使魔军来攻击佛陀,历史上摧毁印度佛教的穆斯林军队和侵扰卫藏佛教的蒙古军队也先后被视为魔军。不管是过去或现在,任何一个藏地派别和寺庙都会定期供养护法并举办专门的法会,祈求护法能帮助他们抵御各种能想象到的外部威胁,保卫坛城的安全。
首先要明确的是,佛教世界的护法实际上是伏魔仪式里被降伏的魔军,莲师神话明确指出这些魔军在被降伏后要盟誓守护寺庙的安全。有了这层背景,我们能看到色达和果洛的地景暗含着对牧民护法身份的确认。在色达,通向珠日莫波和色塘的路上有很多神山被说成是护法,其中最重要的一座是“当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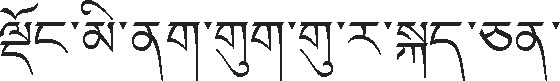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所有试图进入果洛和色达的考察者都以失败告终。1922年3月,英国外交官台克满这样描述色达和果洛:“这片不向……西方人开放的区域是亚洲最未知的区域,信仰未改革的红教……从甘肃回商手里买来的枪让他们比过去更恐怖”(Teichman,1922:77)。当时的西方人认为强调伏魔仪式的宁玛派是藏传佛教最具巫术性的教派,有些考察者在回忆佛堂中那些呈现“忿怒相”的护法时,觉得它们和自己面对的牧民有形象上的关联。这份感觉有它的道理,一些西方考察者听到的关于牧民的记录明显是在暗示与护法的联系。1845年,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听说果洛部落有“吃掉俘虏心脏以增强胆量的习俗”(Huc,1900:101)。1948年,美国探险家克拉克听说它们“是魔鬼的化身……用牛皮绳勒死俘虏,砍头、水淹、割喉、把身体肢解……用箭射,用石头砸,用火烧,或是弄瞎他们的对手”(Clark,1954:33、141)。一个佛教徒会敏锐地指出,这些表述是在形容密宗神明和护法。唐卡艺术里有金刚亥母吞食心识和血浆的造型(象征智慧的增长)。介绍伏魔仪式的文本也经常谈论佛教神明如何砍去魔王的头和四肢。形似罗刹的牧民在皈依后可以依靠他们的胆魄和力量保卫寺庙的安全,牧民们阻碍西方考察者进入坛城或许是在以护法身份降伏魔军。
今天的果洛和色达依然能找到大量运用诗学语言(poetic language)讲述魔军到来的预言,它们号召当地人团结起来保护坛城的安全。今天能找到这些预言文本说明这些伏魔辞藻背后或许隐藏着对历史事件的指涉,这是这些预言被人在公众领域传阅并最终留下抄本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些预言是穆尔克所说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档案域(archival regime),作为特定历史时期汇聚起来的民族档案的碎片,它们承载着由不同语言规则、习惯或意识形态决定的把感知搬向纸面的方式(Mueggler,2011:44-46)。但是对于读者来说,很难仅凭阅读就从这些预言的表述中还原历史的情境,因为它们使用的诗学语言让词与物的指涉(reference)关系在大多数时候呈现开放的状态。但是这些预言的署名者大多是上面谈到的两个密法体系的传承者,由于预言的创作时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早于署名者的出生年月,所以就算有可能是伪造,这些预言也一定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创作的。
实际上,康区佛教在19世纪上半期走向繁荣的原因之一是清朝在完成对蒙古势力的控制后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局势。但是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新龙土司工布朗结的崛起、赵尔丰的改土归流和川甘青军阀的暴政,康区寺庙在极其焦虑的状态下从英、俄殖民者对卫藏的渗透中看到了魔军的影子。如果这是预言存在的背景,西方考察者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来到果洛和色达的。他们的到来让坛城地景更显真实,因为它唤起了一座坛城将面对劫难的设定。有三次考察最能说明欧美考察者被当作魔军,这三次事件的主角是1894年的吕推、1925年的洛克以及1939年的利奥塔和吉尔伯特。与萨林斯解释库克船长之死类似(Sahlins,1985),宗教宇宙观与历史剧的互动让吕推和利奥塔失去了生命。不是说所有闯入者都是魔军,但是外来者越显示对寺庙的威胁,就越容易激发这个想象。基恩(Keane,2003)把人运用符号的方式称作“符号意识形态”(semiotic ideology)。要理解这三次考察如何调动起与伏魔有关的符号意识形态,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佛传故事中一些不易察觉的线索。
八、三次考察简述
在《佛本行集经》里,波旬在袭击佛陀之前有这样一段念白:
今汝比丘,可不见我所率领来,四种兵众,象马车步,诸杂军等……其外复有无量诸龙。各各皆乘大黑云队,放闪电雹,雰霏乱下。时魔波旬,从其腰间,拔一利剑,手执速疾,走向菩萨。(《佛本行集经》卷二十八)
雷电雨雪是魔军袭击的前兆,我们要讨论的三位考察者在遇袭前都遭遇了雷雨,而且都是在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在吕推的案例里,他的队伍在四月到达,藏区寺庙习惯在这时举行法会,以庆祝四月十五号这个释迦牟尼“降魔成道”的日子。吕推队伍里有个叫李默德的队员回忆,在那时,有不止一座寺庙要求法会参加者不能和他们有接触与往来,“喇嘛们说我们是佛陀的敌人和魔鬼的工具……魔军会攻占世界,直到佛陀执剑上马,摧毁他的敌人”(Grenard,1904:136)。在经过路边的帐篷时,队伍里有个俄国队员到帐篷里去借火。这个帐篷挂着一只羊,说明里面有病人,挂在门口的羊是代替病人躲避掌管生死的波旬。但是俄国人不顾村民的阻拦,鸣枪闯入帐篷。在这些铺垫后是夺去吕推性命的大雨,《清实录》把吕推受袭的原因归结为雨后休整时发生的盗马案。但是在盗马发生之前,吕推让手下在寺庙旁练习射击,李默德注意到村民们在他们打靶后变得焦躁不安,所以这些人很可能已经把他们当做威胁寺庙的魔军,这里的盗马也许是驱使魔军离开的办法。最终,袭击者把受伤的吕推丢进河里淹死,这也符合伏魔仪式后处理波旬人偶的方法(Grenard,1904:138-214;《清实录》第五十六册:410)。
在洛克的案例里,他在出发前通过卓尼土司杨积庆找到拉卜楞寺的五世嘉木样活佛,希望他能介绍自己认识果洛的头人。洛克在《国家地理杂志》上谈到了与活佛父亲黄位中(藏名贡布东珠)的对话。黄位中说他“相信世界是平的,中心是一座高山,太阳落山后就有了黑夜”。熟悉佛教修辞的读者能分辨出这里的“太阳”是佛教,这句话是说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南瞻部洲在失去佛教后会陷入愚昧和黑暗。黄位中问洛克是否在一个“人人都长着狗头、羊头或牛头”的地方生活过,洛克说世上没有这样的地方,但是黄位中“礼貌地笑笑”,说“我们的佛书讲过这样的人”(Rock,1930:146、170-171)。在《佛说普曜经》等佛教经书里,魔军就曾被描述为“各各变为师子熊罴,虎兕象龙、牛马犬豕猴猿之形”(《佛说普曜经》第六卷)。洛克或许忘了在卓尼拍摄驱魔仪式时听到的一个说法:在荣赫鹏侵略西藏之后,很多藏族人认为维多利亚女王是女妖的转世(Rock,1928:602-603)。黄位中或许是在询问洛克是否来自英国,这关系到他的队伍是否带有魔军的性质。
洛克之所以想进入果洛,是因为当时的西方人怀疑阿尼玛卿在高度上超过了珠穆朗玛峰(Rock,1930,1956)。在日记里,洛克记述了拉加寺喇嘛在一幅须弥山的壁画前介绍在阿尼玛卿转山时将遇到的神明和护法,洛克相信如果藏族人把阿尼玛卿比喻为宇宙的中心,那么这座山有可能是青藏高原的最高点。他没有意识到他那支全副武装的队伍在坛城里有可能代表魔军。他的队伍在进入果洛时遭遇了雷雨,有好几个部落立刻放话要杀了洛克和协助他的人。根据一位传教士的口述,洛克的队伍本可以走更远,但是他在牧民祭护法时没控制好脾气,踢翻了煨桑的火堆,这个渎神行为几乎当场引发冲突。
利奥塔和吉尔伯特想要穿越的是色达,他们是在迈过当坚这座护法神山时遭遇了大雨。当晚,两人到达了色塘的边缘,这座草原对应须弥山脚下的金轮,跨过这个边界位置就相当于跨进坛城的内核。1913年,色达寺庙在这个位置修建了一座巨型的伏魔塔,塔对面的寺庙在利奥塔和吉尔伯特到来时正举行法会。有人在几公里外就劝告两个法国人不要再靠近色塘,但是他们偏偏选择在伏魔塔旁扎营,仿佛是闯上门的魔军。吉尔伯特觉得这座塔“释放了一些邪恶的咒语,因为从我们看到它的那一刻起,周围模糊的威胁开始变得具体”(Guibaut,1947:95)。与吕推案一样,有人偷走了考察队的牦牛,两个法国人很可能听到了一些与伏魔有关的风声,因为吉尔伯特的回忆录里有一些奇怪的句子:“这些人……在巫师预言和贪婪的助长下……已经让想象力泛滥”(Guibaut,1947:97)。几天后,牧民们杀死了利奥塔,一个堪布在十二年后确认这场伏击以伏魔为目的(苗逢澍、东谷土司,1952:19;李晋,2021)。
三支考察队都觉得他们受到攻击是寺庙有意为之。吉尔伯特听说伏击背后有“迷信的原因”,他甚至想象寺庙仪式“把山川树木中的神灵争取到他们一边,然后借助佛堂中的神灵置我们于死地”(Guibaut,1947:136;Grenard,1904:214)。我们不知道这些猜测有多少是事实,但是把闯入者贬为魔军确实有助于证明佛教寺庙已经把果洛和色达打造成坛城。对于无法用肉眼洞悉的坛城的本体,普通人只能从因果关系的每一次发动和断裂中去感受这个说法的正确;对于把神山等同于佛堂或神明的说法,他们也只能在持续发动的符号解释中把它们加工成社会存在。坛城图式对历史的塑造不仅是佛教修行者走出边界去度化他者的过程,而且是坛城外部的事物不断翻新坛城以重组“地方”的过程。不管是两种方式的哪一种,围绕边界地带发生的想象和移动都是理解“地方”的关键方式。
九、总结:从边缘发现中心
本文在两种纵深不一的历史叙事中揭示坛城话语在青藏高原上的移动。一方面,坛城话语是在许许多多跨越边界的努力中才沉淀在果洛和色达的,藏族佛教徒从中建构出一个从印度到卫藏、康区再到青藏高原最东端的轨迹。另一方面,当坛城话语在19和20世纪影响果洛和色达后,它或许也影响了西方考察者与这片地区的遭遇。虽然坛城图式依托于地方,但是它强调的文野之别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佛教网络的中心都构成了对传统边疆研究的挑战。这里的“中心”不仅仅是人文地理学的“地方”概念预示的社区向心性和粘度,它需要我们调整对区域研究框架的认识,在康区这个汉藏之间的边缘地带发现对文明中心的想象。
我在拼合这个故事时把坛城地景放在坛城图式的整体迁移下来理解,通过在大范围的时空框架下关注坛城图式的流动,我希望以不同于东南亚人类学的方式来扩展人类学的经典论题。在解释坛城时,坦拜亚和格尔茨没有采用流动的视角,他们像涂尔干那样把预先存在的“社会”当做探寻中心和边缘关系的后景。如果沿着这个套路来分析果洛和色达,我们可以说它们是非常完满的“宗教即社会”的证明,因为那里的山川河流、部落政治、寺庙网络和周期性的仪式展演及话语都以环环相扣的方式整合进坛城这个图式。不过在无常的设定下,跨越边界在佛教坛城里有了更重要的意义,它需要我们以更靠近拉图尔而非涂尔干的方式打开“社会”,不再用设定好的“地方”去框定观察的边界。在沿着不断移动的佛魔交战的前线追问什么是果洛和色达时,本文把“地方”看作一个需要被不断打开的后景。
正是在不断打开后景的努力中,我们有机会在相对宽广的维度下深入青藏高原的政治历史变化,由这些变化揭示藏族僧侣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推动。本文阐述的坛城的复制和迁移以更大的政治历史变化为依托。伴随着吐蕃王朝和卫藏佛教的崛起,以拉萨为中心的坛城构成佛教中国化在青藏高原上确立的标志。伴随着安多和康区土司并入近代国家建设的蓝图,物质财富和建庙资本的增长促成两地坛城化的发展。色达和果洛越来越受到国家的关注和宣化,在汉藏政权和地方土司的庇护下,地方修行者把这两个更边缘的地方打造成坛城。接下来发生的西方力量的到来巩固了这个意识。今天,在文化商业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两地僧侣正努力把果洛和色达建设成波及内地都市乃至全球的佛教圣地,或许是为了继续打造坛城的愿景。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像韦伯分析新教伦理那样去思考这些僧侣以何种文化形式融入政治历史过程,并由此建构自己的合法化话语、教派地位和佛教的无常观。我们看到,至少在宁玛派内部,康区僧侣在把自己放置在中心的同时也描述了一个逐渐远离南亚次大陆并靠近汉地的坛城的迁移过程,这个法脉东传过程是藏传佛教中国化在空间上的直观表征。
如拉图尔所言,当我们不再预设什么是“社会”时,“能动者”(actors)也有了更宽广的意涵。拉图尔把“社会”打开成一个可以追溯下去的人和物的勾连。与王铭铭(2015)定义的“广义人文关系”类似,它意味着在人与神、人与物以及人与自然等更宽广的关系中追问坛城的意义和形态,本文尤其刻画了由神话和仪式搭建的人与神明的关系以及人与大地的关系。与西方人类学家在其他地方发现的鬼神想象一样(Taussig,1980;Comaroff & Comaroff,1999;Meyer,1999;Mueggler,2001),伏魔话语、仪式和地景在果洛和色达推动了社会的变化。虽然佛教徒坚称是坛城中心决定了伏魔的方向,把能动性(agency)归结为坛城中心的圣贤意志(intention)。但是在考察者的故事里,雷雨、预言、地景、佛塔等人以外(nonhuman)的因素都是拉图尔所说的促成事件发生的行动元(actant),与卫藏和康区寺庙一起帮助坛城边缘反复再造了已经消失的中心。这种来自边缘的能动性意味着坛城图式的东移是个无可辩驳的藏传佛教脱离印度并实践中国化的过程。
无须赘言,本文只是希望唤起学界同仁对青藏高原上的坛城图式及其蕴含的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关注,未来必将有更细致的对每个坛城社区及其历史进程的研究来替代我所做出的粗线条的勾勒。石硕(2009)和王铭铭(2008)都谈到费孝通对藏彝走廊研究有某种期许。在形容这个走廊地带如何打通民族地区或是华夏核心圈与外圈的边界时,费老有“一子相连,全盘皆活”的论断。坛城图式在融入佛教后先后影响我国的藏族、蒙古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人甚至五台山等汉族地区(郁丹,2015;张帆,2019),这些佛教社区刚好把费老说的“北到甘肃、南到西藏西南的察隅、洛渝这一带地区全面联系起来”(费孝通,1980:157-158)。考虑到佛教对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社会的影响和西方博物学在这个走廊地带的参与,一种有历史厚度的佛教人类学将搭建学术对话的平台和桥梁。王铭铭认为走活费孝通棋局的关键是把汉藏交界地带打造成生产理论的学术带,这是本文运用涂尔干、坦拜亚、格尔茨、拉图尔等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阐释佛教坛城的原因。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安多和康区在18世纪后的变化只是有初步的认识,我们面对的是海量的史料以及支撑它们的民族志知识。我相信对坛城话语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明确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实际进程和表述,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使命下为包容性的中国文明提供更丰富的叙事。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