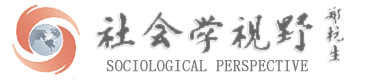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联系电话:010-62511143
京公网安备110402430004号 京ICP备05066828号-1 邮箱:sociologyyol@163.com 网版权所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
|
|
创建中国学派 倡导理论自觉
——纪念恩师郑杭生教授
郭星华
原文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2014年11月9日21点,时间永远定格在这一刻,著名的社会学家、教育家郑杭生教授与世长辞!噩耗传来,学界震惊,人们不敢也不愿相信这样的事实,因为在大家的心目中,郑杭生教授一直活跃在学术的的第一线,讲学、讲座、各种学术会议和活动都有他健康的身影和矍铄的面容;虽说已是79岁的高龄,居然还是满头乌发,令人啧啧称奇;而且笔耕不辍,时有佳作发表,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这样?!当人们回过神来,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的时候,不禁悲痛万分,或潸然泪下,或痛哭失声,唁电、唁函如雪片飞来,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张高丽等,到原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朱镕基、李岚清、吴官正等,再到学界同仁、学生等等,各界贤达纷纷发来唁电表示哀悼并敬献花圈。作为一位学者,称得上是哀荣备极、一生辉煌了。
作为郑杭生教授的学生,而且是在他指导下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我应该写点什么纪念恩师。坐在电脑前,思绪如云、心如乱麻,与先生相处时光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恍如昨日,不禁泪流满面,不能自已。就在2014年10月30日,我还和先生两个人在校内天使食府的三层共进午餐,先生执意付了餐费。当时的先生,脸色蜡黄,步履蹒跚。轻挽先生走回办公室,我心中泛起一阵阵不详之感。一周后的11月6日,先生住进了医院要动手术,我下课后匆匆赶到医院,等他从手术室被推出来时,我快步上前,靠近担架轻轻地叫了一声“郑老师”,他微笑着回答“你来啦”。那成想,这竟然是我们师生的最后诀别,等我中断外地的行程飞回北京的时候,与先生已经是天人永隔!
与先生相识始于1987年7月在贵阳召开的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有幸与先生同赴黄果树瀑布参观,一路上交谈甚欢。先生刚刚荣任人民大学副校长,正是意气风发之时。我被先生洪亮的声音、翩翩的风度、深邃的思想和睿智的谈吐所折服,感到有一股强大的气场在吸引着我。我怯怯地问先生,我能报考您的研究生吗?先生爽朗地笑道,你好好努力!就这样,我198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从此追随先生在学术的道路上跋涉、探寻。
先生是慈祥的长者。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学如何做学问先要学会如何做人。先生待我们如儿女,也言传身教以行动教我们如何做事、做人。因此,先生在社会学界的声望很高、人缘极好,善于团结同志、凝聚力量,有博大的胸怀容忍年轻人的错误。先生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业,也关心学生的生活、工作和家庭。学生遇到困难有求于先生的时候,他总是竭尽全力帮我们解决。读书的时候,我经常去先生家里当面讨教或者处理日常事务,在先生家里蹭饭那是常有的事情。乃至师母对我说,他跟你说过的话,比跟他儿子说过的话要多得多。先生当面的这些教诲将是我一生的财富。
先生是勤奋的学者。400余篇论文,60余部著作,在如此辉煌的成就面前,我等只有汗颜。无论是在担任校领导期间,还是在年逾古稀之后,先生从未懈怠,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写作。先生的办公室与我的办公室只有咫尺之遥,只要没有去外地,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伏案工作的场景,周末也不例外。先生敲击键盘的滴滴哒哒声,宛如一曲曲美妙的音乐,催促我们奋力前行。记得在我读硕士期间,每周六下午(当时尚未实行双休日),先生必定来我们学生宿舍和学生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以校领导之尊常来学生宿舍,令其他同学羡慕不已。
先生是洞明的智者。先生是中国新时期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被誉为中国社会学的一面旗帜,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社会学恢复初期,社会形势纷繁复杂,先生敏锐地指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综合的、具体的社会科学,在随后一系列的研究基础之上,创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运行学派,进而创立了五论,即: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这些丰硕的成果充分体现了先生大师的风范和智者的睿见。
暂抑哀思、厘清思路,我认为先生的社会学学术之路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先生在每一个时期都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独特的贡献。
早期(1981--1993):这一时期是先生思想的成熟期,标志性成果是《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987)、《社会学概论新编》(1987)和《社会运行导论》(1993)。
先生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师。文革结束后,受国家公派,于1981-1983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进修现代西方哲学。也许是机缘巧合,先生在1981年11月8日去英国的时候恰与费孝通先生同机,由于有关方面和家属委托先生在路上照顾费孝通教授,这使他有幸当面聆听到费老许多关于恢复和重建新中国社会学的想法,和费老的交谈,给了他许多直接的启发和启示,这可以算是先生第一次与社会学的近距离接触,也因此在随后的留学英伦期间特意选修了社会学的相关课程。所以,先生的社会学学术生涯应该始于1981年,至今33年。由于先生是文革后第一批国家公派留学的学者,这使他有机会较早地直接感受到中国与西方的差异、较早地直接接触到西方的社会学思潮和理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身经历者,他目睹了文革期间的社会动乱和人性丑恶一面的展示,深感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他一方面借鉴孔德关于“秩序与进步”的社会学思想;另一方面开发我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学术传统,逐步开始形成自己的社会学思想。回国之后,他一边积极筹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一边深入思考、著书立说。
社会学在中国复建之初,面临两个重要的问题。其一是社会学的学科地位问题,其二是社会学的教材建设。对于第一个问题,当时主要的疑惑是:我们有了历史唯物主义,还要社会学干什么?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是什么关系?社会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作用?先生在精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熟悉西方社会学的基础上,对于这个问题作出了十分精彩的回答。他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革命批判性的形态和维护建设性的形态,并明确指出:“社会学是关于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1]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不仅仅需要革命批判性的形态,更需要发挥维护建设性形态的作用。先生当时的一系列论述,为消除极左思潮对社会学发展的恶劣影响,为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确立与稳固作出了重大贡献。先生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的专著《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987)里。
对于第二个问题,编写一批高质量的教材,对于开展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是必不可少的。在重建社会学的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甚至没有一本公开出版的社会学教材。直到1984年,才在费孝通先生的主持与指导下,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国解放以来的第一部社会学教材——《社会学概论(试讲本)》。此后,我国出版的社会学教材如雨后春笋,呈百花争艳的局面。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先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初版),以及之后在此基础上增删、修改、更新的《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初版,2013年最新版)。这本教材在众多的社会学教材中独树一帜,以先生“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条件与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观点为理论主线贯串全书,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全面地、系统地介绍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并根据课堂教学的反映和社会变迁的新情况,对章节安排、教学内容不断进行调整,使之成为当前版本最新、发行量最大的社会学教材,并多次获得国家级奖励。
在厘清社会学研究对象之后,先生开始着力创建他的社会运行学派。他创立的社会运行论,是基于对乱世的切肤之痛,试图探讨一条如何走上社会良性运行之路。在社会运行论中,他不仅对社会学对象问题提出了自己全新的见解,厘清了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与区别,而且全面论述了社会良性运行的条件与基础,系统地探讨了社会运行的机制。社会运行的条件包括物质与精神方面的条件,即:人口、环境、经济、文化、心理;还包括内部与外部条件,即:内部的转型效应,外部的迟发展效应。社会运行机制则包括:社会运行动力机制、社会运行整合机制、社会运行激励机制、社会运行控制机制与社会运行保障机制。先生创立的社会运行学派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专著《社会运行导论》中。这一学派的诞生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也有学者称其为当今中国目前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完整、系统的社会学理论。
中期(1994-2006):这一时期是先生思想的发展期,标志性成果是:《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2005,四卷本),第五卷尚在编纂之中。真可谓:煌煌四百万字,拳拳赤子之心,一代大师的智慧与辛勤尽在其中。
继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运行学派之后,先生即开始着手丰富该学派,先后创建一系列颇具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学界简称为“五论”,即: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社会运行论前面已有论及,不再赘述。
社会转型论,是先生在对当代中国大变革现实的仔细观察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于20世纪80年代末最早提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等概念,试图用这些社会学的理论来概括中国内地社会的巨大变化。[2]根据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特点的分析,先生还提出了“社会转型度”和“社会转型势”两个基本概念。在先生看来,所谓社会转型,就是指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过程。关于社会转型论的主要论述集中体现在专著《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1996)之中。
学科本土论是先生对社会学中国化所作的新的深入研究。在先生看来,“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3]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源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20世纪30初期形成一股本土化的热潮,早期社会学家孙本文先生甚至要将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本土化在当时被称为中国化),作为中国社会学今后的四大基本工作之一。先生力主的学科本土化,可以说是在新时期对老一代社会学家思想的继承与延拓。学科本土论的成果体现主要是专著《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2000)。
社会互构论是先生在研究新时期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先生试图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中具有的基本的和核心的地位为基础,通过对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具体研究,着力理解和解释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关系结构和社会组织模式所发生的转换和变迁,并试图揭示和阐述这种转换和变迁的总体过程和重大过程的本质。[4]社会互构论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深刻地指出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之间互构共变的演变过程。个人与社会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区别构成了相互联系的基础和前提,相互联系本身既是差异的、对立的和冲突的,也是适应的、协调的和整合的,这两方面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的。
实践结构论是先生在研究现代化进程的新特点时提出来的。先生发现,20世纪后期、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古典时代的旧式现代性挥别了过去的辉煌,走向衰落,表现之一是它的两难困境、它的不可克服的鸿沟随处可见:富裕与贫困、发达与落后、繁华与凋敝、兴盛与破败,等等。在这组巨壑汇成的背景之下,凸显出了对和谐的追求—这是古典现代性留给我们的未竟之业,也凸显出了“构建和谐”的时代意涵—这是一个需要付出持续的艰巨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这也标志着以克服旧式现代性缺陷为己任、以和谐协调为标志的新型现代性不可抑制地兴起。古典时代旧式现代性和现时代新型现代性的不同,植源于这里提出的“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有两个维度,即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以及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在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均共同作用[5]。实践结构论的主要思想体现在论文《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新趋势》(2006)之中。
这一时期,也是先生的学生大放异彩的时期,其中最重要的有:获得“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优秀学位获得者”称号的张建明,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励的洪大用,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励的符平,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奖励的黄家亮,获得钱学森城市学金奖的郭星华等等,这些都是先生精心培养、细心指导的结果。其他的学生也分别在政界、商界和学界显露头角、取得成绩。作为他们的导师,先生对此很是欣慰。
晚期(2007-2014):这一时期是先生思想的深邃期,代表性论著是:《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2009),《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2011),更多的将会体现在正在编纂的《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第五卷之中。
到了这一时期,先生已经年逾古稀,但他念兹在兹的是提倡社会学界要追求“理论自觉”,要掌握“学术话语权”,要致力于创立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
先生对学界言必称西方的状况感到深深的忧虑。他秉承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的论述,大力提倡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他敏锐地指出,究竟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学?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还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在先生看来,“中国社会学需要的是对西方社会学的借鉴,并主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实际,进行原创性的或具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例,一个验证。”[6]这样的“理论自觉”,才是与中国从地区性大国走向世界性强国、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边陲走向世界学术中心之一的趋势相吻合的。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学界仍在对西方社会学理论不加分析地顶礼膜拜、亦步亦趋,先生的论述无疑是有振聋发聩的警示意义的,也展现了先生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走向未来、走向繁荣的一种担当与责任。
如何才能实现理论自觉进而达到理论自信?或者说,为什么我们长期以来缺乏理论自信?因为学术话语权不在中国人手里,我们早已拱手让给了西方。先生深刻地指出“学术话语权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深层要求之一。”[7]作为“权力”的学术话语权体现了权力的非强制性特征。其传递符号、思想、知识、信息,以柔性、无形的方式来弱化强制和压力,消解权力可能引发的反感和敌意。这一过程提升了权力的吸引力、降低了权力的代价和成本。作为权力的学术话语权主要有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等类型。先生分析道,“历史和时代给学界提出了要求,即更好地掌握学术话语权,并在理论自觉基础上达致学术话语权的制高点。这是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格局边陲走向中心的一条必由之路。”[8]其实,不仅在社会学学科领域存在这样的问题,其他学科领域的情形何尝不是如此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先生晚期思想的影响是跨学科领域的,是我们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写到这里,已是凌晨时分。初冬的北京,已经是寒气逼人,萧瑟的景象平添了几分哀伤。再过5个小时我就要到世纪坛医院为先生启灵,并护灵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先生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念及此,心如刀绞,今夜注定无眠。先生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著作等身、成果丰硕,给后人留下了享之不尽的精神遗产;先生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和社会学研究;先生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他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人生高度,他高尚的品行和人格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别了,先生;别了,恩师!愿先生安息,愿师母宫延华女士健康长寿。特献上一副挽联,以志纪念:
哀翘楚功已成志未酬梵界从此添贤圣
哭先生鬓未秋身先死人间何处觅恩师
2014年11月15日凌晨 学生星华泣笔
作者简介:郭星华,湖南湘潭人,1957年出生,教授、博导,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法律社会学、城市流动人口等等。
[1] 郑杭生:《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光明日报》,1985年7月29日第3版。
[2] 参见: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第20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第33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参见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第59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参见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新趋势——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6] 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7] 郑杭生:《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8] 郑杭生:《学术话语权与中��社会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