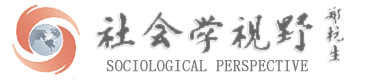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联系电话:010-62511143
京公网安备110402430004号 京ICP备05066828号-1 邮箱:sociologyyol@163.com 网版权所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
|
|
农村人口外出流动模式与农村老人养老困境
谷玉良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长沙410081)
摘 要:乡城人口流动加剧了农村老龄化程度,也导致农村老年人养老的诸种困境。不过,人口迁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也存在诸多不同的模式。从流动规模和定居意愿的角度来看,乡城人口流动分为个体流动、家庭化流动与举家迁移定居三种模式。不同的流动模式对于农村家庭结构以及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的影响,在逻辑和程度上显然是不同的。研究从乡城人口流动的不同模式入手,讨论不同乡城人口流动模式下农村老年人所面临的具体养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走出困境的可能途径。
关键词:流动模式;农村老人;养老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一直以来,农村老年人养老以子女照料与土地供养为主要模式。该模式以家庭养老为特点,子女负责老年人的物质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养老服务。农村居家养老模式建立在土地依赖的基础之上,而多人口的家庭结构则为居家养老提供人力和基本的经济支持。
农耕社会中,农业种植是农民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的主要来源。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之上,为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提供了时空便利[1],也因此衍生出农村养儿防老的传统家庭养老观念。同时,由于人口流动性较低,农村家庭结构相对稳定,家庭人口数量相对较多,主要以联合家庭为主。存在较为普遍的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联合大家庭。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全国有老年人口的家庭户中,老年人与成年子女等亲属生活在一起的有6764万户,占有老年人口户74.73%,其中三代户又居绝大多数,超过95%的农村老人靠家庭赡养。多代人口的聚居为家庭养老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方便了子女对老年人的就近供养。而子女的就近居住也很大程度上分担了老年人养老负担。应该说,土地依赖与联合、扩大的家庭结构是农村传统家庭养老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不过,持续不断的乡城人口流动极大动摇了农村家庭养老的社会基础,给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带来极大冲击。从土地依赖方面来看,目前我国有超过2.7亿农民工,其中外出农民工接近1.7亿人。农村流动人口对土地的依赖性明显下降,接近40%的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将土地流转出去[2]。农民对土地依赖性的下降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流动性,从而给农村家庭养老带来了时间与空间上的冲击。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也极大破坏了传统农村联合家庭结构。导致农村家庭结构进一步小型化、核心化。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2000-2015年间,我国家庭户内人口规模已经从3.44人下降到2015年的3.1人。“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破坏了农村传统家庭结构,增加了农村老人养老困境”[3],也弱化了家庭养老的功能,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了农村老年人抚养比。研究表明,“因人口城乡迁移,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将由2008年的20.84%快速上升到2025年的50.04%、2034年的81.93%、2047年的102.09%”[4],农村老年人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养老问题[5]。
乡城人口流动加剧了农村老龄化程度,也导致农村老年人养老的诸种困境。不过,人口迁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也存在诸多不同的模式。从流动规模和定居意愿的角度来看,乡城人口流动分为个体流动、家庭化流动与举家迁移定居三种模式。不同的流动模式对于农村家庭结构以及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的影响,在逻辑和程度上显然是不同的。研究从乡城人口流动的不同模式入手,讨论不同乡城人口流动模式下农村老年人所面临的具体养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走出困境的可能途径。
研究选择山东省西南部5个外出务工人口较多的村庄作为调查地点,以实地访谈和电话访问的方式,在2016年10月至2017年8月间,前后四次共调查了121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具体调查对象情况见下表1:
表1: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迁移模式 |
户数 |
老人留守户数 |
老人随迁户数 |
|
个体流动 |
83(68.6%) |
83 |
0 |
|
家庭化流动 |
26(21.5%) |
26 |
0 |
|
举家迁移定居 |
12(9.9%) |
7 |
5 |
二、个体流动与农村老人养老问题
个体流动指的是那些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单独外出,进入城市务工、经商,通常以家中的男性劳动力为主。个体流动东是乡城人口流动在早期阶段的主要流动模式之一。近年来随着家庭化迁移数量的增多,个体流动进城的农民工比例有所下降。但从笔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农民工个体流动总体上仍然保持较高的比例,达到了68.6%。
实地调查表明,农民工之所以保持个体流动的模式,往返于城乡之间,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家中有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或者有正在上学的子女,需要妻子留守家中照顾;其二,经济条件差,无法负担举家迁移或家庭化流动所需成本;其三,妻子无劳动技能,无法找到合适工作;其四,家中尚有土地,农业种植负担仍然较重,需要男性劳动力季节性返回乡村处理农业种植事务。或者有的家中在经营少量土地种植的同时,还有禽畜类养殖副业,需要夫妻双方中一人留守经营。
由于是个体循环流动,流动农民工的父母不存在随迁可能。这里,将老年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的,另外一种是需要子女经济上援助供养的。从实际调查情况来看,个体循环流动模式中,打工者家庭中有14.5%的老年人仍然外出打工,有41%的老年人虽然不外出打工,但在农村通过土地经营仍然有部分收入,能够满足基本生活所需。这部分老年人年龄基本在60-67岁之间。而那些因年龄过大或身体存在疾病等失去了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所占比重为44.5%。其养老基本上靠子女供养。
从实际的养老状况来看,那些自我供养的老年人,由于经济上有一定的劳动收入,且身体上无重大疾病,因此不需要子女额外的身体照料,但其子女对其缺乏必要的情感关怀。而那些年龄较大或因疾病失去了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在养老方面,子女对其养老主要负责经济援助、身体照料和适当情感关怀。
从老年人自身的主观养老需求来看,自我供养的老年人,养老主观态度表现出对经济上的一定程度的需求,以及对情感关怀的普遍较大需求。造成其养老方面情感关怀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老年人经济上自足、身体上健康。因此,其子女在主观上对其养老问题关注较少。另一方面,由于是个体循环流动,夫妻一方中的留守者(普遍为妻子)负有相对较重的家务、农业和子女抚养教育负担。因此,对于老人的日常情感关怀相对缺失。而对于那些由子女供养的老年人来说,由于本身子女对其承担了经济援助,总体上老年人对当前的养老状况基本满意。但仍然有部分老年人表示,存在一定的身体照料和情感关怀需求。其养老满意度相对不高的原因,与打工家庭留守人员家庭事务负担较重、赡养老人精力不足有直接关系。
表2:个体流动模式中老年人养老情况
|
|
实际养老状况 |
老年人主观养老需求 |
年龄段 |
占比 |
|
自我供养 |
经济基本自给自足;身体无重大疾病;偶尔帮助子女家庭从事农业劳动;情感关怀不足。 |
暂无长远养老规划;需少量经济援助、情感关怀需求较强 |
60-67岁 |
55.5% |
|
子女供养 |
完全经济援助、适当身体照料和情感关怀 |
基本满意(68%) |
67岁以上 |
44.5% |
|
身体照料·情感关怀(32%) |
在对养老的未来规划和态度上,当被问及“当年龄更大,失去劳动能力后,养老怎么办?”时,个体流动者家庭中的老年人对自己未来养老普遍缺乏明确规划,且相当一部分老年人满足于当前养老现状。主要原因在于“子女家庭条件还不够好,不想给他们增加额外负担”。这在独立生活、自我供养的老年人中表现的尤为普遍。不过,调查显示,无论是自我供养的老年人还是由子女供养的老年人,都对于子女情感关怀普遍有较强的需求。
而从外出务工子女的角度来看,绝大部分外出务工子女对自己父母的养老问题有自己的规划,但仅限未来父母失去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阶段。而且,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最能接受和自己最愿意规划的父母养老模式是父母单独居住,自己每天定时照顾和看护,或者有能力者送父母到养老院养老。而且,大部分人对于当下父母的情感需求缺乏足够的重视。
三、家庭化流动与农村留守老人负担问题
家庭化流动一般包括同代流动和二代流动两种形式。同代流动即夫妻二人共同外出,二代流动即夫妻二人携带子女同时外出。近年来,家庭化流动的农民工数量越来越多。据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流入地的家庭规模为2.61人,与2013年相比,流入人口家庭规模增加了0.11人。超过一半的家庭有3人及以上同城居住,跨省为2.54人,省内为2.75人。从居住时间看,2015年,居住3年以下的流动人口平均家庭规模为2.29人,居住3-4年的为2.70人,居住5年及以上的为2.95人。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也显示,我国农村流动人口两代户数量已经占流动人口总量的38.52%。北京的农民工同代迁移(主要指夫妻双方)和二代迁移(主要指夫妻双方携带子女)数量已经达到农民工总数的65%[6],个别地区,如湖北省的家庭迁移农民工的比例甚至高达84.4%[7]。
不过,从笔者所调查的几个村庄来看,农民工家庭化流动的比例尚未达到全国平均数。实际的家庭化流动数量占全部被调查家庭的比例只有21.5%。而从流动家庭人口规模来看,夫妻二人外出流动务工的有19户,夫妻二人携子女进城务工的有7户(其中,两个子女的有两户,另外5户为独生子女家庭),平均家庭流动人口规模为2.35人。
从外出务工家庭结构及其人口特征来看,夫妻二人外出务工的19户家庭中,单独一个孩子的家庭有8户,两个孩子的有11户。其中孩子最小的为4岁,最大的为19岁。外出务工者家庭中子女在就读高中以下的有15户。这15户家庭中,子女年龄在4-15岁之间(乡镇教育局统一规定小学入学年龄为7岁);子女就读高中及以上的家庭只有4户(子女年龄在16-19岁)。夫妻携子女进城务工的7户二代流动家庭中,子女年龄在12-21岁之间。其中,双子女家庭中,两户家庭皆为其中一个子女在18岁以上,且辍学后随父母一起打工。
了解外出务工家庭结构及人口特征,对于我们理解家庭中老年人实际养老状况及其主观养老需求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外出务工者家庭结构及其人口特征对家庭中老年人养老状况有重要影响。具体来说,家庭化流动进一步缩减了农村传统家庭人口规模,降低了农村家庭老年人的养老质量和水平,导致老年人养老过程中的贴身照料和情感关怀缺失,对于那些丧偶老人来说更甚。同时,那些同代流动或二代流动,且有留守儿童的家庭,儿童看护和照料,以及房屋照看和家务劳动等任务由青年人向老年人的转移,也极大增加了老年人身体和心理负担。有些老人甚至还承担起外出务工子女留在农村的土地经营和农作物种植任务。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导致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老龄化,劳动负担从青壮年人口向老年人口转移。这些处于养老年龄的农村老年人,普遍表示压力较大,身体和心理都承受了严重考验。同时,部分留守老人还承担了对孙辈的看护和照顾任务。不过,“也正是由于隔代抚养容易导致留守儿童产生心理、行为、情感等偏差问题”[8]。因此,外出务工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容易出现紧张化与矛盾冲突。
对于绝大部分留守老年人来说,在儿子儿媳进城务工时,帮助他们照看家庭和孙辈,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义务和责任,并且对于子女进城务工表示支持,体现出了较强的牺牲精神。农村传统文化中为了下一代牺牲的理念在老年人身上有充分的体现。
“有哪个做老(农村俚语,指父母)的不希望子女生活更进一步、更好呢。他们现在有了好的机会出去打工改善生活,那是他们的福气。我们这个年龄了不能给他们做更多的贡献,照看家庭和孩子,这也算是力所能及的事,还能发挥点余热。压力肯定是有,身体越来越不如以前,也有点力不从心,那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在外面闯荡也不容易,都是为了下一代。”(ML20170803)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老年人对于子女进城务工普遍表示支持,且愿意自我牺牲为外出务工子女承担家庭看护与孙辈照料责任。但大部分老年人对于自己未来的养老仍然有一定的期望。他们寄希望于自己的牺牲能够换来子女未来为自己养老提供更多的支持。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当前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表3:家庭化流动模式中老年人养老情况
|
|
实际养老状况 |
老年人主观养老需求 |
年龄段 |
占比 |
|
同代流动 |
外出务工子女给予经济支持;实际负担孙辈生活照料和家务劳动;少量农业种植劳动;身体负担较重,心理压力较大,生病无法得到子女及时照料。 |
对子女的牺牲精神遮蔽了养老需求;对未来养老缺乏明确规划;对子女养老有较强的期望。 |
60-65岁(84.2%) 65岁以上(15.8%) |
73.1% |
|
二代流动 |
送养老院;情感关怀少 |
对当前养老状况基本满意,有情感关怀的需求。 |
70岁以上(14.3%) |
26.9% |
|
部分老年人独立生活,部分为外出务工子女看护房屋;子女给予适当经济援助;无生活照料;情感关怀少。生病时无法得到子女及时照顾。每年节假日定期返乡探望老人。 |
情感孤独,有较强的情感关怀需求;未来养老规划不明确,对子女养老有较大的经济援助和生活照料期望。 |
60-70岁(85.7%) |
人口流动带来了农村家庭结构的进一步小型化与核心化,但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村老年人赖以养老的主要模式。因此,成年子女对父母养老的态度和看法,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质量和水平。从调查情况来看,那些同代流动的被访者普遍对自己父母的付出表示感激,也理解自己外出务工给年老父母带来的身体与心理上的负担和压力。并且表示在父母养老方面“一定会尽更大的责任”。而经济条件的改善,则为其给老年人提供更优质的养老服务奠定了条件。不过,有约63.2%的人表示,经济条件改善后会送父母到养老院养老。在他们看来,养老院能够给家中老人提供更优质的老年看护服务。需要指出的是,在养老院养老方面,老年人的主观认可和接受程度仍然不高。在他们看来被子女送养老院养老,有一种“被抛弃感”,认为子女没有尽到自己的养老照顾的责任。并且认为会被其他村民嘲笑“老了没人管”。当然也有部分老人接受并且愿意到养老院养老。认为,在子女有经济能力的条件下,“去养老院养老可以减轻子女贴身照料的负担,让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打工赚钱和改善家庭条件上来”。
而对于那些二代流动者来说,留守父母养老问题也成为他们急需解决的棘手问题。夫妻进城务工携带子女,除了成年辍学子女可以打工帮助家庭提高收入外,大部分是为了改善子女的教育条件。且这部分外出打工者的外出务工时间一般较长,在5年以上。家庭条件相对较好,但仍然不足以满足接老年人进城养老。这部分人普遍表示,目前父母的留守是一个过渡阶段,“未来经济条件允许,愿意接父母进城养老”。
四、举家迁移与随迁老年人地方依恋问题
总体上来说,当前农民工举家迁移城市定居的比例不高,而老年人随子女迁移城市定居的更少。据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老人健康服务专题调查显示,当年度我国流动老人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2%,年龄中位数为64岁,其中约有八成低于70岁(其中,60-64岁约占54%,65-69岁约占24%),70-79岁的占18%,80岁及以上的高龄流动老人不到5%。当然,流动人口不仅仅指进城务工农民,除此之外还包括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流动人口。因此,扣除城市间流动老人,由农村进入城市,跟随务工子女进城的农村老年人数量相对较少。
对鲁西南5个村庄的调查来看,老人随迁到城市养老的比例仅占全部被调查者的4.1%。而在举家迁移城市定居的农村务工者家庭中,也有超过半数的人没有随子女定居城市。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迁往城市定居的子女家庭本身住房条件无法为老年人提供额外的住房需求。二是老年人自己不愿意前往城市定居。而这部分留守农村的老年人,也表现出与二代流动家庭相类似的养老情况,以及面临类似的养老困境。
那些随务工子女进入城市定居的老年人,从其随迁的原因来看,照顾晚辈、养老与就业是老年人口随迁流动的三大主要原因。数据显示,在三中流动原因中,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为与子女团聚或自行异地养老的比例为25%,仍有23%的流动老人因务工经商而流动。从笔者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农村老年人随子女迁移进城的原因主要为照顾晚辈和养老。迁移家庭良好的经济条件是支撑老年人随迁的基础。老年人随子女举家迁移到城市定居的案例中,迁移家庭一般为在外长期打工,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收入的家庭。7户举家迁移者家庭中的中青年夫妻普遍有稳定工作,家庭年收入都在13万以上,最高的年收入的30万以上。且其中有6个家庭是独立经营的个体户(包括5户老人随迁家庭),比如开餐馆、商店和汽车修理店等。5个有随迁老人的举家迁移家庭中,有1个迁移到了省外居住,3个从农村迁移到了本地区地级市城市,还有一个迁移到了本省其他地市城市。
从随迁农村老人养老的情况来看,主要以居家养老为主。进入养老院、敬老院、光荣院、福利院、老年公寓等机构养老的农村老人几不存在。居家养老虽然方便子女就近照顾,但本质上属于异地养老的范畴。在异地养老的过程中,农村随迁老人也出现了诸多不适应的问题。这其中对家乡的依恋以及城市参与不足所导致的无归属感,是随迁农村老人面临的最主要养老问题。
案例1:儿子儿媳在这里好不容易打下点基础,生活稳定下来,接我过来养老是他们孝顺。但在城市里总觉得自己一点用没有。农村人闲不住,老了也一样。平时他们出去上班,我想在家里帮着收拾收拾家,但家里很多东西都是他们收拾好的,方便他们随时用的。我怕收拾乱了他们不好用,给他们找麻烦,也不敢去动。想接送孙子上学下学,外面都是车,方向也掌握不准。他们也不放心,不让我去。每天吃完饭就是看电视,上网也学不会,无所事事。也没有认识的熟人,一天下来除了早上、晚上,说不了几句话。活的不自在,还平白给子女增添了很大的负担,不如在原来农村更自由。(FG20161003)
案例2:现在一家人都到城市来了。老家里他们(儿子、儿媳)的房子是卖了,地也卖了。我自己的还留着。前两年来的时候他们让我也卖了,我坚决不卖。这是我过了一辈子的老家,死了我还得回来,坚决不能卖。来城市这两年,每年我们两个(老年人夫妻俩)都得回老家待一阵子。每次回去,原来关系比较好的老哥、老弟、近房(表亲),见面了,说不上几句话,眼泪就下来了。不是城市里的生活不好,是城市没有这些亲友关系。虽然孩子在那里有自己的家,但叶落归根,他们不回来我也回来围着父母(农村人死后有进祖坟的习俗)。到这个岁数了,在外面飘荡着,总不是滋味。(MW20170223)
虽然有学者指出,从个人迁移到举家迁移的转变是农民工流动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农民工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必然结果。不仅如此,举家迁移还能够避免个体迁移所造成的留守社会问题[9]。但从被访者的讲述来看,���活条件和养老环境的改善,并未明显提高随迁老年人的养老主观体验。农村与城市在社会交往与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是他们在晚年养老生活方面面临的主要困难。而乡城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引发了随迁老人浓重的乡愁和思念情绪,为他们带来了一定的心理问题。
因空间距离引发的对老家和乡村的思念,在空间社会上也被称为是“地方依恋”。空间承载着人类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在空间中的互动与实践使人们对所处其中的空间形成稳定的记忆。一旦远离曾经所处的空间,对空间的记忆便会从人的头脑中显现出来,并表现出对特定空间的念想。图安将这种对特定地方和空间的念想称作“恋地情结”[10]。“恋地情节”是人们对特定空间或地方的一种精神依恋,即某个特定地方被认为是人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并对其持有持久浓厚的情感[11]。“地方依恋的对象可以是具体的空间、物体、一个人”[12],甚至是象征性的意义等[13]。案例2中,随迁老人对落叶归根理念坚持和对农村老房子、亲友等的思念,就表现出了对农村的象征性意义和具体对象的依恋。而案例1中,随迁老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不适应,以及由此对农村生活的怀念,除了生活习惯外,主要还与社会交往缺失有关。在特定情况下,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可能超过了特定的地方,直接导致地方依恋[14]。城市生活所缺少的农村熟人之间的交往,正是激发随迁老人思乡情绪的直接原因。
地方依恋是由距离产生的类似乡愁的情感所引发的个体情绪[15]。个体所处的位置与特定空间的距离越近、访问频次越高,地方依恋的强度越强[11]。不过,根据笔者的调查显示,迁移距离较远,尤其是跨省流动的随迁老人,其地方依恋的感觉要远强于省内流动老人。而那些在本地市内流动的随迁老人,由于距离较近,且重返故乡访问较为容易,因此其地方依恋感相对较弱。也就是说,随迁老人对于故乡的依恋强度,基本上随迁移距离的增加而增强。
地方依恋所产生的消极情绪是随迁老人异地养老不适应的主要表现。显示出农村老人普遍存在严重的安土重迁思想,包括城市老人在内皆是如此。因此,“极少有老年人愿意随家庭迁移异地养老”[16]。而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则加剧了老年人的地方依恋感。比如,大多数流动人口并没有被纳入城镇养老保险体系中来[17],导致随迁老人也容易生发出给子女增添负担的心理压力;随迁老人对城市缺乏社会认同和归属感,社区参与程度较低,生活满意度普遍不高等[18]。
五、总结与讨论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务工,破坏了农村传统联合家庭结构,导致本就日趋核心化的农村家庭规模进一步缩小,严重削弱了农村家庭的居家养老功能[19]。西方国家一些研究也指出,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会因子女外出而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空间距离拉大,导致家庭中能够用来照顾老年人的人数减少和家庭养老质量降低[20]。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人口流动模式的差异,有可能导致农村老人在养老方面面临不同的困境,笔者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个体流动与家庭化流动的模式都造成了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但在内容和程度上则明显不同。相比较个体流动,家庭化流动的农村家庭,其养老问题更为严重,尤其是那些二代流动的家庭。而老人因子女举家迁移而随迁到城市养老,虽然避免了出现留守老人所存在的养老问题,但却存在老年人因乡村依恋而产生消极情绪的养老问题。因此,在关注农村流动人口家庭老年人养老问题时,必须考虑农村人口流动模式的不同所造成的差别化的养老困境。
从乡城人口流动的发展历程来看,本文所划分的人口流动模式差异,既可以视为是一个横截面差异,也可是看作是一种纵向渐进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差异。当前,城镇化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持续快速推进。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将逐渐趋向家庭化和举家迁移。因此,未来农村流动人口家庭中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将更集中的表现为生活方式与社会交往的适应性困难,以及由此造成的充满消极情绪的对乡村依恋问题。
针对调查的发现,以及当前农村流动人口家庭中老年人养老问题,应该有针对性的思考应对举措,才能做到精细化与科学化。
首先,个体流动的农村家庭,其老年人养老所面临的问题相对要小,主要在于缺乏未来养老规划和情感关怀。而专业社会服务组织如社会工作机构等,在帮助老年人制定未来养老规划方面能够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家庭内部留守妻子及老年人应增加日常沟通,进一步提升相互理解和情感交流,以满足老年人情感孤独需求。
其次,家庭化流动的家庭,留守的身份造成了老年人的身体与心理负担、生活照料困境和情感孤独问题等。而且,老年人与子代之间缺乏就养老问题进行的沟通与规划。加强老年人与流动子代之间就养老问题的沟通与交流,能够有效增进两代人之间就养老问题的理解,并达成共识。同时,专业服务机构,如社会工作组织等的介入,也能够帮助双方更好的交流,并在老年人养老规划上做到科学化指导。此外,需要特别注意对老年人关于养老观念的调适。在整个社会家庭结构核心化与小规模化的前提下,机构养老是未来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养老的主要实现模式。农村老年人机构养老,也是解决当前流动人口家庭老年人养老问题,减轻流动人口负担的重要措施。组织老年人集中了解当前养老现状,鼓励有条件家庭老年人参与机构养老,能够有效解决当前留守老人养老问题。而构建政府、企业、个人多元养老费用分担机制,以及非盈利机构与专业服务组织的介入,也能够极大减轻农村老人养老经济负担,并提升其养老服务水平和质量。
再次,举家迁移家庭中的随迁老人表现出乡村的依恋问题,实质上是对城市养老的不适应。造成这种不适应的原因主要是城市社会交往的缺失,以及因帮不上子女忙给子女带来压力而产生的负疚感。因此,解决随迁老人的上述养老问题,必须从老年人养老需求和心理调适入手。必须注重鼓励老年人社区层面的参与积极性,通过组建各种形式的老年人兴趣小组和团体,来调动随迁老人社区参与和社会交往的积极性。同时,专业社会服务组织和NGO组织应积极介入,帮助老年人合理度过由生产生角色向养老角色的顺利转变。特别是老年社会工作者,在调动老年人积极性,挖掘老年人潜力,发挥其生产性作用和社会价值方面,能够起到有效作用[21]。
参考文献:
[1]唐钧.人口流动颠覆农村家庭养[J].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015(11): 13.
[2]陈旭峰,田志锋,钱民辉.农民工土地流转的现实可能性研究——基于山东泗水县的调查分析[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2011(5): 24-28.
[3]戴卫东,孔庆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村养老保障的双重效应分析——基于安徽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状况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 2005(1): 40-50.
[4]刘昌平.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的战略思考[J].西北大学学报, 2008(4): 23-28.
[5]欧阳功林.人口迁移流动下的农村居民养老问题探究——湖北省潜江市村庄的典型调查[J].中国市场, 2016(6): 254-256。
[6]洪小良.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 2007(6): 42-50.
[7]石智雷.家庭化迁移有助于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N].中国人口报, 2013-05-13-003.
[8]宋卫芳.隔代抚养对幼儿社会化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人民论坛,2014(8): 165-167.
[9]高健,孙战文,吴佩林.农民工家庭迁移状态的演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山东省
951户的调查数据[J].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4(8): 106-112.
[10]黄向,保继刚, Wall Geoffrey.场所依赖(place attachment):一种游憩行为现象的研究框架[J].旅游学刊, 2006(9): 20-23.
[11]Kyle, G. Bricker, K. An examination of recreationists' relationships with activities and settings[J]. Leisure Sciences, 2004(26): 123-142.
[12]Johnson N C. Public Memory. James S. Duncan.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M]. Cambridge: Blackwell, 2004, pp.316-327.
[13]Tedman, R. C. Is it really just a social construc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to sense of place[J].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2003, 16: 671-685.
[14]Chow & Healey, M. Place attachment and place identity: First-year undergraduates making the transition from home to universit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8, 28(4): 362-372.
[15]Knez I.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for places[J]. Memory, 2006, (14): 359-377.
[16]丁志宏.我国老人异地养老意愿的实证研究.兰州学刊, 2012(6): 129-133.
[17]郑秉文.改革开放年中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发展与挑战[J].中国人口科学, 2008(5): 2-17.
[18]刘亚娜.社区视角下老漂族社会融入困境及对策——基于北京社区“北漂老人”的质性研究[J].社会保障研究, 2016(4): 36-43。
[19]王慧敏,李保东.人口流动下的农村家庭养老[J].黑河学刊, 2005(4): 120-122。
[20]Hugo, G.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 the family in Indonesia. APN Workshop on migration and the family in a globalizing world[M], Singapore. 2001.
[21]陈雯,江立华.老龄化研究的“问题化”与老人福利内卷化[J].探索与争鸣, 2016(1): 68-71.
责编:ZP